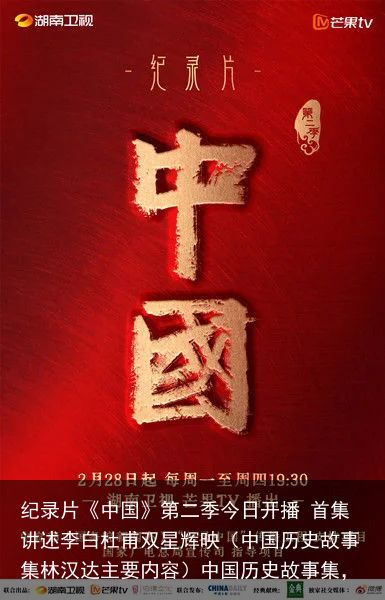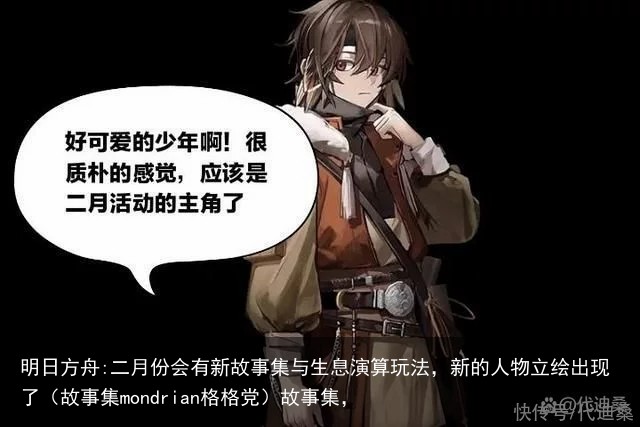你听过哪些奇诡的民间精怪故事?(精怪故事集 豆瓣)精怪故事集,
我感觉什么东西藏在床单下。我屏住呼吸,拉开被单。
被单里黏黏腻腻,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田螺壳。
床尾,一个长发女孩从深不见底的螺壳里爬出来,自我两腿间向上爬……
1
知道田螺姑娘吧?
给做饭、收拾家务,分文不取,乐于奉献那个。
我村里出了个小子,真去找田螺姑娘了。
耗了三四年,真给他找着了。
也不知啥情况。给人家姑娘百般哄骗,拐进了家门。
转头,关上房门,硬逼人家做了自己老婆。
这田螺姑娘没的挑,盘亮条顺,害羞爱笑,平日里没别的爱好,就爱做饭、打扫。
就是晚上关上屋门,没一点动静。
我们打趣这小子身体不行。
可这小子却一天比一天瘦。
我们又劝他婚后收敛点,别放那么开,日子还长。
他也不说话,就垂着头,跟听不懂人话似的。
后来,他就越发不对劲了。
刚开始,他老揉眼睛,一揉就揉出来好多小籽似的东西,粉红的,一捏就碎。
看了医生,医生俩字:「沙眼」。给开了红霉素眼膏。
可眼膏没效果,粉籽沿着他眼周长了一圈,密密麻麻地布满眼眶,最后眼睛都睁不开了。
我们劝他去省里大医院看看。
没想隔天,那些粉籽不仅从他俩眼皮上,还从嘴、鼻孔、耳朵眼儿里溢出来……
尤其是他一说话,粉籽就直往外喷,溅了我们一身。
他走两步,道上都是粉红色的籽,随风吹得到处都是,田埂里有,水沟里也浮着。
谁也不敢靠近他,找他说话。
后来,村里调皮的小孩结伴去看他,回来吓得哇哇大哭,魂不附体。爹娘找婆婆给招魂去,这才说出话来。
原来,那小子已经整个人都给裹在粉籽里头了,还跟那儿傻笑呢。
他老婆就坐在炕头上,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瞅着那几个偷看的小孩。
小孩说,他们看见的,不是个女人,是个大螺丝。
我们心里也害怕,就拿上家伙事上门去看。
一进门,粉色的籽就跟海浪似的,瞬间给我们浇了一身。
几个人给粉籽闷了一嘴,呸呸呸吐出来。
我们赶紧动手,把粉籽都给扫出去,那小子不见人,只见他老婆坐在炕头上,一直笑着瞧着我们。
那笑,那眼神,真是吓人。
我们中有个胆儿肥的,指着她吼:「你他妈是个啥子东西?!你不是田螺姑娘!」
这话一出,那女人忽然哈了一口气,眼瞅着在我们面前伸展起来。
衣服皮肤化成一个螺壳,自螺里一点点伸出粉红色的胶状触须。
螺里,一个女人懒散散地说:
「我不是田螺,我是福寿螺啊。」
早上一到事务所,这篇日记就装在信封里,不声不响递进了门。
我读完后,手边的螺蛳粉立刻不香了。脑子里全是福寿螺,以及它产的那堆籽。
翻过信封一看,匿名,没填收件人。
说它是日记,就挺离谱,不真实。可要说是故事,它又没头没脑,跟地摊小说似的,透着一股子「怪力乱神」味。
但,它讲的一定是螺分村里发生的那桩怪事。
是我今年最大的,也或许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案子。
螺分村全村 88 户,187 名男性集体失踪案。
不是天灾意外失踪,是突然地、集体地,人间蒸发那种失踪。
想想我头皮就发麻。
倒不是吓的。
我是个保险调查员。做我这行,夸张的事没少见,胆子也够大。
可一想到消失的 187 个人,上了意外险的就有 47 个,每个都要赔付 50 万……
这才叫他妈的吓人。
这 187 人都是在四年前的秋天失踪的。
顺便说,《民法通则》第 23 条规定:当公民因下落不明满 4 年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
名义上,这 187 个人都死了。
实际上呢?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47 户人家的女眷全部要求索赔。
猫腻到透着股子臊味儿了。
是不是躲起来骗保的?
寄出这篇东西的是谁?
男的女的?是不是螺分村人?
要是男的,就也是失踪人口之一。
要是女的,保险索赔人几乎都是妻子、母亲又或女儿,这女的就是想要保费吧?
是不是故意给我使绊子?
为了搞清楚事实,我得自己动身探一探。
2
火车转大巴,换乘三蹦子,我来到螺分村。
村子三面环山,主要民房都盘踞在半山腰上。上山的路窄,没人维护,两侧树都要歪在公路上了。
刚进村口,没见到人,只看到一些个顶子歪斜,破破烂烂的瓦屋。
房门和窗户都关得死紧。
黄昏时分,我一个人都没遇着,不知不觉走到一个三岔路口。
突然,我听到「吱呀吱呀」的声音,耳根都酸了。
循着声音过去,发现村子一口井,一个老太太正打水。
这老太太很奇怪。
她像把一柜子衣服都穿到身上了,从头到脚就没一处露出来的,只剩俩眼珠子死死盯着井口。
「老太太,村公所在哪里啊?」
她没反应,只一个劲地压那口水井。
这井不太对劲,听着里头没水声。我往井里头一看,黑黢黢的,冒着寒气。
一般一口井打三丈深,可这井好像不止三丈似的。
抬眼一看,正和老太太打了个对眼。她一双小黑眼珠直勾勾盯着我。
我一个肝颤,大着胆子又问了她一遍,她还是没反应,可能是个聋子哑巴。
我转过头去,忽然听她嘴里咕哝了一声。
「你说啥?」
「呸古吕……」
我一头雾水。
「呸古吕?」
「呸古吕。」
复读机。
我摇摇头,搓搓手臂,心想得赶紧找个地方落脚。
这村子给我奇怪的感觉。
房屋树木也好,老太婆也好,都不怎么现实。像突然做了场噩梦,进了某个粗陋玩具打造的小村庄。
最终我找到了一间挂着招牌的招待所。多半是村里唯一一家。
不是瓦屋,而是一间结实的石砖建筑,两层楼高。
敲门后,门嘎吱一声,打开条缝,露出半张人脸。
「你是保险公司派来的?」
是个女老板,说的是带口音的普通话。
我硬着头皮点点头,女老板啪地把门关上了。
糟了,难道我要露宿?
半分钟后,门又开了。
女老板穿着一身围裙出现在门后,一半脸被头巾遮着,另一半脸面无表情。
「拿身份证登记。不能扫码,只能用现金。」
我在一层小柜台前付了押金。
说是柜台,也就是老式写字桌,上面放了账本和一台老式电视机。
要不是我掏出手机看看时间,真以为自己回到三十年前了。
我说:「可吓着我了,我以为你也是索赔人呢。」
「我是。」她说。
这下更尴尬了。
我胡扯:「就是走个形式。要是真调查,就不会只派我一个来了。」
女老板不回应,只塞给我一个洗脸盆,又把一个尿壶塞到我腋下,房间钥匙则「哐啷」一声掉进尿壶。
「抱歉。手滑。」她说。
我觉着她不是手滑。
我爬上二楼,从尿壶里捏出来铜钥匙,打开了左手边的房间。
拉下灯绳,昏黄的光照亮房间,墙皮剥落,露出里面潮乎乎的石灰墙。
窗户打开,能看到迎面扑来的深绿色大山和森林。
我望着窗外,胡思乱想。
古怪。
我一路走来,仅有的田地都荒芜了,果树也蔫的。
即便男人都消失了,女人也会种地,没道理放着钱不赚。
窝藏人是不太可能了。
没人会故意把村里的男人赶进大山,整整四年,就为了骗保。有这时间,进城打工,怎么都挣到钱了。
我本想问女老板有没有晚饭,但下去看了一眼,她人也消失了。
只剩下老式电视机上播放着一部叫《田螺姑娘》的动画片。
我有点蒙,走出门看了一眼,忽然发觉山林的颜色越来越暗。
本来太阳要下山了,山色变暗很正常,可不知为什么,等山林映出黑色以后,我才有一种「确实在山里」的感觉。
而山里,是什么都有的。
突然从脚心升起一股寒意,我缩了缩肩膀,回了房间。
上楼前,我瞥了一眼电视。电视上正播放一个画面,小小的螺壳里,蜷缩着一个长发赤裸的女孩。
镜头越拉越远,我看到螺壳前面围着许多人。
每个人都和螺壳里的女孩差不多大小。
我后脖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原来那不是个小螺壳,那螺壳有一人那么大。
我赶紧回到房里,心想着不做多余的事,等太阳升起来,立刻干活,争取快点走人。
我换上睡衣,拉开被单。
忽然,窗外窸窸窣窣的,有奇怪的声音。
我拉开灯仔细看,看不出端倪,像是树影在摇晃。
窗外没有路灯,望出去,除了被屋内灯光照亮的树梢,什么也看不见。
——可外面看得见我。
我突然冒出这么个想法,马上把窗帘拉上。
可是我窗外有树吗?我怎么记得没有呢。
当下冷汗哗啦啦地直流,我轻手轻脚缩回被子里。
窸窸窣窣的声音还在不断传来。
这次,是从我床垫里。
我感觉什么东西藏在床单下。我屏住呼吸,拉开被单。
被单里黏黏腻腻,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田螺壳。
床尾,一个长发女孩从深不见底的螺壳里爬出来,自我两腿间向上爬。
她浑身淌水,像刚从海里爬出来,脸上、手上密密麻麻挂满细小的螺壳。
我还没尖叫,她比我先一步张大了嘴。
粉红色的籽从她嘴里涌出来,喷在我身上。
顷刻间,我满头满脸都是粉籽,粉籽从我口、鼻、耳朵各个缝隙里灌进去……
我出不了声,像溺水一样,挣扎着,一下坐了起来。
晨光从窗帘缝隙洒进来。已经是早晨了。
我身上睡衣全湿了。
还好,是噩梦。
我起来,洗了把脸,把这些破事都归在那个日记上。
自从读了那个东西, 就老做噩梦,日思夜想。
赶紧解决完吧,我赶紧走人。
吃了早饭,我出门去村公所,赫然发现村公所背面就是档案馆。
想调查失踪人口,档案馆肯定是第一选择。但档案馆关门了。
村公所里只有一个大妈在看守。说是看守,也就是看电视、织毛衣。大妈是个编外人士,管事的都下山办事去了。
大妈说:「男人不敢留螺分村太久,怕被诅咒。」
「诅咒?」
她看了我半天,忽然说:「我以为你也是住大白楼,找那个罗小姐的。」
「罗小姐又是谁?」
我真一头雾水。
大妈语气古怪:「罗小姐啊。她来螺分村以后,男人轮着千里迢迢来找她,可是个稀罕货。」
我再也问不出什么消息,就登记了一下,大妈给了我把钥匙,我成功打开了档案馆的门。
一打开,门里吹起一股尘土,我咳嗽半天。
可能大半年都没人打理了。
不要提电脑录入系统了。纸质材料捆绑在一起,累在角落,都发霉落灰了。
我找到相关村民的档案,拣了几本县志,又挖了一些新闻报道。
大多记录都断在了四年前。
我花了大半天工夫,一直到太阳即将下山,做出了一整套统计结果。
没算错的话,螺分村从宋高宗那个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这里,有八百多年历史了。
县志和新闻报道记录里,总共记载了 87 起居民失踪案件。没有记载和丢失的部分,就难说了。
所有失踪的人均为男性。
有的是父子突然失踪,也有兄弟们结伴失踪的。
事件之间,相隔短的有三四年,长的有十数年。没有规律可言。
每一起案件失踪的人数也不定,我粗略统计,不知道有没有比这次失踪人口还多的情况。
收起统计的册子,我忽然感觉浑身发冷。
我的统计不是给上面的报表,不是算账。数字后面都是一个个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人……
这意味着什么?
来之前,我以为这起失踪事件里隐藏着什么猫腻。但想不到,这样的失踪现象在螺分村由来已久。
村子一直在持续出生,持续消失人口,但没有人觉得奇怪。
我想到这里,突然有点透不过气,起身走出档案馆抽支烟,对着夕阳吐烟圈。
脑子里有什么一晃而过,又抓不住。
我重新读了一遍手机拍下的日记。
「……我们赶紧动手,把粉籽都给扫出去,那小子不见人,只见他老婆坐在炕头上,一直笑着瞧着我们……」
我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点:人们打开房门,清扫粉籽出去时,那个丈夫消失了。
或许,螺分村男人们失踪,和这个有关?
我脑子里出现了那个诡异梦境。
螺壳里的女孩……
我脑袋上都是冷汗。
不敢往这方面去想。太玄了。
我回到档案馆,忽然发现桌上除了一堆资料,还放了张便条。便条写得简单,字迹秀丽。
「请来白楼与我们见面。罗。」
罗?我忽然想起来,难道是大妈提到的那位罗小姐?
我们?除了她还有谁?
我转过头去,观察档案馆的构造。
刚才短短十几分钟里,我一直站在馆外。
除了正门,只有与前面村公所连接的侧门可以入馆。
我试着推开侧门,纹丝不动。这扇门是锁死的。
我回到村公所,值守大妈已经不见了,只有毛衣和针散落在椅子上,灰色的毛团像极了梦里螺壳的形状。
3
我心里虽然有些瘆得慌,但还是劝说自己:早九晚五嘛,大妈也该下班了。
我现在就去找罗小姐吧。
可白楼在哪里呢?
我感到纳闷。出了档案馆,我爬上小山坡,眺望整个村子。
螺分村除了住家、田地、果林,只有那片森林我进不去。
村子绵延不断的瓦房,像小型长城,隔开了森林与田地,如一圈子巨人手牵手,把森林挡在外头。
森林看似面积不大,却一直延续到山头顶处,再往前走是悬崖峭壁。
我观察了好一会儿,才发现白楼在哪里。
怪不得之前没注意。白楼根本称不上楼,只是个三层无外饰的白板子建筑,得和瓦屋建筑太不一样了,反而灯下黑。
它正修在森林边沿处,远处山谷悬崖边了,底下是万丈深渊,真不知道住的人是什么心态。
我走近白楼,它比远看体积更大,正面没窗户,侧面只各开了一扇窗。
我敲敲门,一个女人开了门。
内部窗户都拉着很厚的窗帘,没开灯。我看不清女人的长相,只感觉很年轻。
「是罗小姐吗?」
女人在阴影中似乎笑了笑,侧身把我迎进来。
白楼里面特别简单,像装修了一半,涂了墙皮,拿两件家具进来就完事了的办公室。
一层是一间不大的会客厅,有一组皮沙发,一个小玻璃茶几,上面搁一盏台灯。
我就着台灯看了罗小姐一眼。和想象中不同,她不是什么绝世妖姬,只是个相貌清秀的普通女人。
即便如此,我对她印象还不错。毕竟这村里女人都板着一张脸,紧绷绷的,只有她有个笑脸。
罗小姐给我倒了杯茶。
我进入正题:「那便条是您写的吗?您有什么贵干?」
罗小姐把手指放在嘴唇边,又指指楼上。
「李博士在睡觉。他早上刚退烧。前两天感冒了,发展成肺炎,在屋里打点滴。但他一直惦记着你的事。」
「我?」突然提到我,吓得我在沙发上坐正。
「对,你的事。你是×公司调查员,负责调查螺分村,对吧?」
我纳闷:「你们怎么知道的?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是李博士的意思。具体要问他,我只是个助手。」
我继续追问,罗小姐就耸耸肩说:
「他的研究和螺分村有关。剩下的你问你们保险公司吧,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我掏出手机,发现信号几乎没有,就问她楼上信号怎样。
「三楼,那里有个窗口。」
我顺着一道窄梯爬上去,在二楼走廊上看到一张靠窗边桌,桌上有部座机。
既然连了座机,怎么不用呢?
我试着拿起话筒,一听,里面没有声音。顺着座机往下看,发现电话线断了。
我感觉奇怪,但心里还惦记着给公司汇报,就没细想。
三楼只有一条狭窄的走廊,一边有一扇窗户,打开窗户,我借着断断续续的信号给公司打了通电话。
公司告诉我,李博士确实收到了公司支付的报酬,我遇到问题尽可以找他。
我这才放了心。
本来还感觉那罗小姐有些诡异,但既然公司这么说了,我这种打工人也不会挑肥拣瘦,尽可以逮着他们要求帮忙。
忽然,楼梯间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
一个瘸了腿,全身裹着雨衣的人从楼梯爬上来。
因为瘸腿,他只能一节一节慢慢爬,但他的速度一点不慢,也不见喘,几乎没什么呼吸声。
我想叫住他,他却一声不吭,独自拐个弯,进入走廊深处的房间。
三层就一扇窗户,我使劲往他的方向看,也看不清顶头的房间里有什么。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刚还没闻到什么,可他打开门进去的瞬间,我闻到一股子奇怪味道。像腥臭味,又像是腐坏了的食物。
我正要跟上去看看,忽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我带你到处去看看吧。但不经允许的地方可不能进,是博士说的。」
罗小姐不知何时已悄然走上来。
我吓了一跳。她人虽然瘦,但也不至于一点脚步声也没有吧。
真是古怪的女人。
我解释说看到一个奇怪的瘸腿人走进房间。
罗小姐听完,一脸疑惑:「这里没别人啊。」
「……你别吓我。」
她却一脸严肃,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开玩笑。有个帮忙的阿姨,送食材和打扫卫生。她不认识你,肯定不理你。」
我隐约觉得哪里透着不对劲。只是罗小姐显然不是嘴松的人,继续追问也没结果,我决定转个话题:
「你说可以带我在村子里到处看看?」
「是啊。我来这里半年了,什么都熟了。」
我把村公所大妈说她是「稀罕货」的话重复给她听。
罗小姐微微一愣,叹了口气说:「这里的女人没见过男女同工同酬,以为一起工作的男女就不清不楚。你住久了,她们也会拿你和我来说三道四的。教育高的人都去城里了,这里的人啊……」她摇摇头。
我装作理解似的点点头,只注意到一个问题:除了她口中的李博士,还有别的男人来过螺分村。
我不敢多想,收敛心神,把注意力投向窗外:
「那边森林里都有什么?」
「那边啊……」
她要说什么,忽然,我肚子咕噜噜响起来,先一步打断了她话音。
这下是真的尴尬。我中午啥都没吃。
她笑了,说:「眼见为实,正好我要做晚餐,去摘点果子,你可以跟我进林子看看。」
我点点头,正想看那林子里有没有可能藏人。
我俩走出白楼,她带我爬了楼后一小段坡路。我这才发现白楼背后有一条小径,可以直入森林。
一踏进森林,一瞬间,光线就被遮蔽在外面。
已经是深秋了,森林里的灌木没一点发黄,仍是暗绿色的。树枝叶子垂到我肩上,我吓一跳,以为有手在拍我。
脚底下都是腐叶,底下泥土软硬不一,深一脚浅一脚,踩陷进去了,就闻到一股子难以言喻的腐臭腥味。
我寻思这地方也不是果林,摘哪门子果子?
走着走着,林中竟突然出现一片空地,中间像剜了一勺土地似的凹陷下去,一棵巨大的果树从底部长出来。
树干有三人合抱粗细,形状如巨掌朝天,手指狰狞向上,枝子上长了密密麻麻的金黄果子。
我看一眼,瞬间眼晕,浑身鸡皮疙瘩都立了起来。
树哪会长这么密的果子?
「这是什么树?怎么这么大?」
「金橘树。」
「我没见过这么大的金橘树,一般一整棵树花盆都装得下。」
罗小姐笑了笑:「螺分村的金橘树不一样。从北宋时起,螺分村就向京都进贡水果。这种古树和现在的树苗树种不同,生长百年千年也不在话下……只是被人遗忘了。」
她说完,忽然抱着树干向上爬了一截:「来。帮我接着。」
她摘了一把金橘,随手向我抛来。金橘打在我脸上,滚了一地。
「瞧你,没干过农活吧?」
我赶紧在地上拣金橘,她不断把金橘抛下来,我四处拣,西服四个兜装得满满的,实在装不下了,只好对她喊停。
「真拿你没办法,好吧。回去了。」她说。
采摘橘子这一会儿,我和罗小姐之间的关系说变就变。突然从平等,变成上下关系。她像一个年轻妈妈,而我是个没长大的儿子。
森林有奇怪的原始性,我们走进来之前,还是文明社会的合同甲乙方,进了森林,就变成具有支配关系的男女。我是被支配的一方。
我警觉起来。罗小姐有些古怪的魔力,让人拒绝不了她。
这种古怪的感觉一直延续。
不知是不是耗费太多体力,我上山的时候都没那么费劲,下山却呼哧带喘。
罗小姐还是一脸轻松,爬山和下山时都没流汗。
下坡走到三分之一,罗小姐忽然转回头去。
「怎么了?」
罗小姐指指路的一侧,那里有一道浅浅的水渠,像是连通了森林深处的水源。
可能是螺分村的人自己引出来灌溉果林的吧。
「水花生。」罗小姐说。
她一直脸上挂笑,很少像现在似的拧紧眉毛。
不知是季节还是什么缘故,水渠里水不多,流速极慢,水渠边长着一些手掌般形状的绿叶植物。
「怎么了?」
罗小姐摇摇头:「水花生太多了。侵入物种爬上山了,金橘要受害了。」
「不至于吧。扯掉就好了。」
我随手扯了一把这些植物。
罗小姐还是摇头:「水花生有毒,旱涝不怕,冷热不忌,是『世界十大恶性杂草』。你扯掉它,留一点茎下来,它也能继续长。越拔,它就越扩散。喂给牲畜,牲畜的粪便里都会留籽,继续繁殖……」
我咋舌:「好顽强。」
罗小姐也笑了,笑得跟之前不一样,有点深意。
「是啊,真顽强。」
回到白楼,罗小姐进厨房十多分钟,出来时端了一大碗汤。里面有黄橙橙的金橘,还有一些粉红色的肉片。
「这什么肉?」
「螺片。」她动作温柔地搅动汤水,「现在田螺养大了,可以吃了,都和金橘一个大小了。」
我看着粉红的螺肉,滚烫的汤水流动起来,肉好像会颤动似的。
像活的。
我咽了口口水,不敢吃,但又抹不下面子,就喝了几口汤,吃了两个金橘。
很古怪,入口很甜,但又说不出的让人抗拒。
罗小姐一脸关心地看着我。
「你下山的时候好像很累,现在好些了吗?肠胃有没有不舒服?」
她问得突然,我感觉奇怪,只敷衍:「没什么啊。天晚了,我先回接待所了。」
「你不如搬到我们这里住吧。我和李博士两个人,到了晚上都没人聊天。」
她一直邀请我,我下意识拒绝了。
现在,我已经确定森林里很难藏人,没必要一直留在白楼。
罗小姐把我送出去时,我再三让她不必送了,她仍坚持给我送回招待所。
路上,我们又经过了村里那个三岔路口。
老太婆还在「嘎吱嘎吱」地压水井。
我忽然想起刚入村时,老太婆跟我说的话。
我问罗小姐:「你通这里的方言吧?」
「懂一点。」
我问「呸古吕」是什么意思。
罗小姐歪着头,手指点点下巴:
「她说,想见儿子女儿。看来是空巢老人太寂寞了。」
「呵,这方言有意思。短短一个词就有这么多含义了。」
「是啊。」罗小姐笑了,笑得特别温柔,简直让人忍不住想相信她。
但是,她真能骗人。
我都知道她在骗人,可不知为何,就是没法当面戳穿她。
我回到招待所,看到女老板在拖地,仍旧挡着半张脸。我好奇她的脸为什么遮着,可想到万一是火灾留下的疤痕,我就尴尬了。
我问她:「之前有多少外人,尤其是男人来住店?」
「不少,一拨又一拨的。」
女老板的语气一点也不高兴,她挣得到钱,有啥不高兴的呢?我寻思。
除非,她干这个活,就不是本意。
她说,来到螺分村的人「一拨又一拨」,那这群人里,至少得有几个是调查员,又或者至少能传递出来一点消息。
那为什么在我来螺分村之前,没查到一点相关的调查结果?
还是说……他们来了就没回去?他们……也消失在了螺分村?
我脊背凉飕飕的,感觉这么胡思乱想下去就更不妙了。还是干脆利落地出一份调查报告,然后赶紧回家,把这些破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刚要上楼,忽然又想起来问女老板:「你们方言里『呸古吕』有什么意思?」
女老板停下手里的活计,顿了一顿。
「意思是……要来了。」
4
早上醒来,我一头栽在地上。
翻身起来,什么也看不清。
刚开始,我以为是睡迷糊了,洗了把脸。手摸到眼皮时,从眼角捏出什么东西。
凑近了看,是一些粉籽。
我打了个寒颤。
错觉,是错觉,眼屎而已。我给自己两巴掌,保持清醒。
洗干净脸,眼睛还有些模糊,但不影响视力了。
不管怎样,先和李博士谈一谈。他昨天一直休息,今天也该起来见人了。
出门时,我忽然看到女老板在砍树。
她砍的是些不大的金橘树苗,看似轻轻一砍,树汁飞溅,一大摊红色液体洒在地上。
我吃了一惊:「卧槽怎么回事?树怎么流血了?」
女老板:「这种东西见到了要立刻砍掉,不要犹豫。等它长好了,别的就都别想长了。」
我继续问,她就不说了。
我走到白楼,罗小姐已经站在门口看着我了,脸上还挂着笑。
我看见她就心慌。她像个不会疲劳的机械,眼睛里没一条血丝。
罗小姐:「李博士想见你,但不能时间太长,只有五分钟,他很容易累。」
我点头,跟她上楼去见李博士。
李博士住在二楼紧里面的房间,那是个套件,外面的小会客室里摆了双人椅和屏风。
屏风底色漆黑,像刷了层柿油,上面画了一株巨大的金橘树。金橘的密度激起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等待片刻,罗小姐推着李博士从卧室出来。停在屏风另一侧。
罗小姐:「你不要太靠近。他见风就发烧。」
李博士只有三四十岁,但头发白了一半,身上裹着层层衣服,像很冷似的,戴了口罩和帽子,只有一双眼露在外面。
罗小姐对着李博士的耳朵说了几句话。
我颇为尴尬,赶紧把目光移开。
这时,我发现李博士还一直盯着我。他的目光很奇怪,一眨也不眨。
李博士说话了。声音轻而无力。
「螺分村的人集体消失,是因为一种病。」
我没想到他开口就是这个,问:「什么病?」
「一种会导致他们想自杀的病。你听说过集体歇斯底里症吗?」
「没。」
「1374 年,德国亚琛暴发过最著名的一次集体歇斯底症。患者会突然跑到街上跳舞,几小时、几天、几个月也不停,直到他们死于力竭、心脏病抑或中风。
「这是一种不治的传染病,发生在特定人群之中。螺分村的情况,显然特定的患者都为男性。」
我怎么听怎么不对劲:「退一步讲,这种事有可能发生。但螺分村不止这一起失踪事件,我查过,有记载的就足有 87 起。」
「那历史上就发生过 87 次。」
李博士语气很冷漠。
他忽然咳嗽了几声,罗小姐回过身去倒茶。
这时,他忽然抬眼瞪着我。嘴里还在一个劲咳嗽,一只手却从袖子伸出来,悄悄指向天花板。
他手指枯萎得不像正常成年男性,但我一瞬间理解了。
「三楼。有异常。」
等罗小姐回过头来,我俩又各自盯着墙或地面,装作无事发生。
「很感谢贵公司联系我,但请回复他们,我改主意了。酬金我会退回去。结论无偿送给您。」
他说话像很费劲,但这几句话,愣是一刻没停说完了。
罗小姐:「瞧你这么着急做什么,汗都出来了。」
她从屏风后端来个洗手盆,拧了一块湿毛巾,擦李博士头上和手上的汗。
一般人在人前做这种私密举动,多少都会显得僵硬,或者迅速敷衍了事,可她却做得极慢、极细致,擦完,她还拿出护手霜,一挤……
一瞬间,我嘴里反酸。
那护手霜里挤出好多粉籽。她把粉籽抹到李博士两只手上和手腕上,转头看向我说:「挤多了,你抹一点吧。」
我因为意想不到,根本没躲开,被她一抓,抹了满手的油。
我赶紧缩回手。她笑了起来,笑声中,我越发感觉恶心,背着手把黏腻的油抹在裤腿上。
「我先告辞。有事之后会来拜访。」
我匆匆下楼,闻了闻手背,只闻到一股护手霜常用的茉莉香。
可能我看错了吧。不管怎样,刚刚李博士确实暗示,三层藏了什么。
罗小姐不想让我看,但李博士的想法正相反。
下楼时,我瞥到瘸子正走进屋里。我闪身躲在楼梯间,看他在一层角落里搁了一袋东西,又一瘸一拐地出去了。
我凑上去扒开袋子一看,里面满满装得都是拳头大小的螺丝。
那场面真的难以形容。
我没忍住,跑进后院,哇的一下就吐了。
吐了满地的粉籽。
我脑袋都蒙了,抹抹眼睛再一看,发现不是什么粉籽,只是一地酸水,胆汁都出来了。
白楼后院边上有座独立出来的厨房,厨房外垒起了小山一样的螺壳。
可能罗小姐就那样,拿起一个个螺丝,挑出肉,放进锅里,慢慢煮成汤……
我又吐了一口酸水,这才匆匆跑出门。
我一眼看到瘸子在屋门口喷农药,农药上标着「使它隆」。不知不觉,白楼前生出好多水花生。
这个瘸子真可疑啊。穿雨衣,不露脸。罗小姐说这是个「阿姨」,可我怎么看他的姿势都是个男人。
如果他是个男人……
我叫他:「喂——」
我话音还没落,瘸子忽然掉头就跑。
他一跑,我就想追。
一个瘸子,必然跑不过我。我两三步撵上去,从后扯住他的雨衣。雨衣「刺啦」一声裂开,一个男人扑倒在地。
我凑上去一看,我多年训练出来的人脸记忆力不会骗我,立刻认出了他就是 47 名投保人之一的……
「齐六!」
齐六脸色紫青,看看我,爬起来还想跑,我一把扯住他后领。
「你骗保来了?我他妈告诉你,你没死!没失踪!不能领保险金——」
我眼前一晃,带着肥料的铁锹猛地向我砸来。
还好我反应快,松开手躲避了致命一击。
齐六已然反客为主,抄起家伙追赶我。
我吓得一扭头沿着坡跑进了森林。
钻进林子的一刹那,我感觉森林都摇摇晃晃的,无数影子和可怕的颤动向我涌来。
我绊了两跤,一路摔进了森林的坑洞里,正好就是罗小姐带我来摘果子的那棵大树。我躲在大树后面,眼看着齐六追上来。
但他一面向大树,立刻抛下铁锹,对着大树一通跪拜,好像见了祖宗一样。
他磕了好几个响头,掉头就跑,一次也不敢回头。
我心说他是疯了吗,这又不是祖坟。
抬头一看。
巨大的金橘树上长的根本不是什么金橘……而是一个个拳头大的福寿螺。
福寿螺像极了繁茂的果实,低垂下来,对着我吐籽。
5
我逃回招待所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但我整个人眼前都黑的。
那棵大树和齐六的跪拜,绝对有什么诅咒效果。
我一个劲地给公司总部打电话。
手机打不通,我情急之下,找到女老板,告诉她我都看到了什么,求她快点报警。
说着说着,我一低头,鼻血像泉水似的流下来。
我身上的劲也跟着没了,膝盖一软,跪在地上,当着女老板的面,哇的一下吐出一堆东西。
这回我看清楚了。是一大坨粉籽。
我人都呆了,女老板却没有。
女老板拿了扫帚把粉籽扫出去,又出门抓了一把水花生,放灶里烧成白灰,和面粉调匀,兑了点茶,让我喝了下去。
「水花生是药,狗牯脑茶合这里的水土。喝了就舒服了。」
我他妈这能是水土不服?
但我感觉很虚弱,就没抵抗。喝了两口。奇怪的是,这偏方对我好像真管用,喝下药后,不那么反胃了,眼前也清晰了许多。
我问:「森林里到底怎么回事?那些人都怎么了?」
女老板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
「他们都中了邪,中了螺分村螺神的邪。」
「螺神?」
我脑子嗡了一下。
女老板:「我们都说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它在这里长了千年,万年了。我外婆、我母亲、我自己,都是它的傀儡。
「你来了,就出不去了。走出去时,你就像其他男人们一样,会变成它们的养分。」
6
「你到底知道什么?现在最好赶紧讲出来,要不就出命案了!」
我威胁女老板说。
女老板倒是没抗拒,只说:「都是我小时候,从我妈那里听来的故事。」
……
接下来我要说的,不能写下来。
只能由外婆传给母亲,母亲传给女儿。
都是口头传说。
谁也不知道,是谁编的、谁传的,有多少是真的。
千万年前,我们这些小人儿,都还只是泥地里的小鱼儿的时候,螺神就在这里了。
螺神从黑乎乎、望不到边界的地方飞来的。
那地方极其寒冷。我们这样的肉体凡胎,在那里冒个头,就冻成冰碴子,灰飞烟灭了。
螺神到了这里,只是休息一阵,也被外面的世界折磨得筋疲力尽。
它钻进这片土地的深处,睡起了大觉。
它睡了千年、万年,想要等恢复了体力,继续回到那个无边无际的地方。
它降临的时候,立刻发现了我们。
我们那时,才刚刚从黑沼泽里长出手来,爬上岸。
螺神吞掉了我们中的一部分,又告诉另一部分:
「你们要继续产出更多的养分给我。我允许你们充分地繁衍。」
我们这些女人听了,都遵从了它的教导。
以前的事太古老啦,已经没人记得了。
但是在螺分村里,千万年来,女人都是螺神的仆役,男人都是螺神的养分。
我们女人心里只有个影子。我们不敢拿出来谈,只能在炉火边上,用一些个小故事跟孩子们传递这个秘密。
但绝不会讲给男孩子听。
因为,太残酷啦。
螺分村里,一旦生了男孩,这户人家就会忧愁个一年半载。
我们从来不给男孩太多钱,资助他们上学。
因为男孩但凡开窍了,就要出村子去赚钱。可还没出村口,就一下变成螺神的养分了。
真可怜啊。
我们说,他们只是回到螺神的怀里去,以后大家都要去的。
但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觉得,他们大概就这么死了。
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这回事的。
我本来不怕什么神怪传说,我妈跟我说的那些,我一点也不信。
「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人搞这种迷信呢!」
我瞒着家里人出了村子,出去上了初中,读了两年书。
可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回来。
外面活不下去啊。
我们这些螺神的女人,到外面去,就好像脱了壳子的螺肉,很快就病恹恹的。
只能回来了。
一直到去年,那个罗小姐和李博士,带着他们的基金来到村子里。
又是抽血又是做什么活检。
我们给折腾得够呛。
不过是一百来个男人失踪,你们怎么这样没完没了?
难道外面的男人,就不失踪吗?
真的……不失踪吗?
……
我听女老板说完,逐渐心惊胆战。
本来我也不想信,可我现在还在一个劲流鼻血。
我擦擦鼻血,问她:
「你说的,离开了螺分村就像『脱了壳子的螺肉』,是怎么个说法?」
女老板半天不答。
我以为她不肯说了,却看她撩起挡着半边脸的头巾。
我看一眼,就一下从椅子上滑了下去。
她一边脸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螺。
那些螺把皮肤和肌肉揪成一团,她一说话,那些螺像活的一样,颤颤巍巍地活动起来。
「要不是有这些螺趴在我脸上,我半边的肉都融化了。我回来得还及时,它们是来救我的啊。
「螺神,还需要女人来生男孩,喂养它们呢。」
我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充满震撼。
怪不得那四十几个索赔人习以为常。
她们知道当男人想要离开村子,就会化作满地的螺丝,变成那东西的养分。
7
我确定女老板把她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我心里的震撼特别大,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呆呆地走到门外,坐下透口气。
我想起齐六想敲死我的模样,也不敢走出院外。
抽了支烟,做了点总结。
面前两条路。
一条,是不管不顾,管他大爷的螺丝附体的,开走女老板的三蹦子出山去。生死未知。
另一条,是相信女老板的话,现在绝不要跑出山去,不能做螺神的养分,待在村子里自救。
我对女老板的话半信半疑,可我做调查员这行,最忌讳莽夫思维,有一点矛头都得查个清楚。
我走回去问女老板,能不能打电话联系外面。
女老板摇头:「昨天为止还能。今早开始,信号没了,电话线也不通。」
看来,有人给村子通信掐断了。
我脑子里冒出罗小姐的身影。瞬间胆寒。
她是知情的。她的所有举动都带着一股子怪异色彩。
那李博士呢?他查到什么了吗?
李博士对着我指指三层的手势。
他一定已经有了些结果,才没有立刻成了螺神的养分……
但他明显已经行动不自如了,可能被罗小姐绑架了。
罗小姐是什么来头?李博士又研究出了什么?
好歹我也不算一个人跟她斗,先找到办法去看看李博士留给我的线索再说。
天色渐渐黑了。齐六可能会告诉罗小姐我发现他身份的事。
那样我和罗小姐表面的和谐就撕破了。我不敢说,我能打得过她,总感觉她身上有点特别的东西。
我回到房间,点了点自己随身携带的东西,看有没有什么可做武器的。
瑞士军刀一把。
手电筒一把。
一包烟、一个打火机、一台手机。
盘点一下就感觉自己出来得仓促,军刀拿出来,居然卡壳了。想多来把武器,就只能抽皮带了。
我脱掉不利于行动的外套,简单把裤腿和袖子用绳子包扎好。
我一出门,女老板就在门口堵住我。
我警觉起来:「你想干嘛?」
「你想做什么,我帮忙。」
我不怎么信她,只敷衍说出门探探情况。
她说:「你最好让我帮你。有我在,你就不用担心齐六。」
「为什么?」
「我是他老婆。」女老板冷冷地说,「我帮你也就为了这个。那个混账王八蛋……挣钱不行,家里也不干活,全他妈只靠我一个,还跟大白楼那儿腻着,整日的不回家。」
我恍然大悟:「你想把他撵回家来?」
女老板点点头。
这下我脑子里倒是立刻冒出了个主意,跟她说了,她没怎么犹豫就点头同意。
当下,我和女老板赶去了白楼。她走前门,我绕道后院。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她在前门外头大吼,嚷嚷着:「齐六你给老娘出来。
「出来!姓罗的狐狸精!」
女人都是天生的演员,女老板演得不错,果然,没一会儿齐六就瘸着一条腿现身了,我看到二楼晃出一条影子,罗小姐显然也下了楼。
我趁机翻进一层的窗户,摸黑顺着楼梯上了三楼,一直钻进最里面的房间。
不用撬锁,房间根本没锁,一拧就开了。
一瞬间,一股难以言喻地腥臭扑面而来。
我闻过孤独死老人的尸臭,闻过实验室福尔马林的味道。但没什么味道能和这个东西比较。
它不会立刻让人吐出来,但闻一会儿,我怀疑自己鼻子坏了,后半生都没得救了。这味道就伴随我了。
我做了点思想准备,仔细看里面的情况。
顿时,我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房间和底下李博士那个套间一样大小。但中间打通了,放了各种各样的设备。整个房间都在嗡嗡作响。
有无菌传递舱、储液装置、循环风机……
地上没有盘好的线路交错在一起,我不小心绊了一跤。站起来,正对上无菌舱里一样东西。
准确来说,是一大块肉。
还活着,会动。
肉上面长出一条触须一样的东西,触须顶端有个婴儿小手般的东西。
无菌舱上接进去一副手套。我试着把手伸进去,触了那小手。
小手立刻抱住我的手套指尖,一整团肉跳动起来,如心脏一般搏动着,急于把我的手包裹住。
我想缩手,它包裹得越来越紧。
我慌起来,突然看到,这一坨肉底下居然有个小小的螺壳。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它是螺。一个螺的螺肉。它来自于那么小的一个壳,它已经缩不回去了。
他妈的是个大螺丝。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