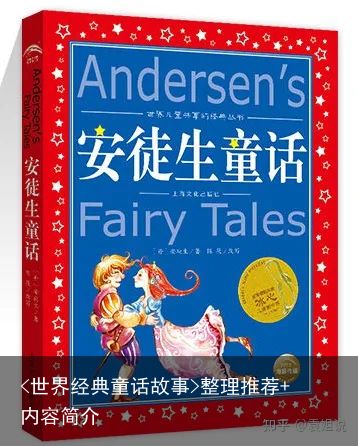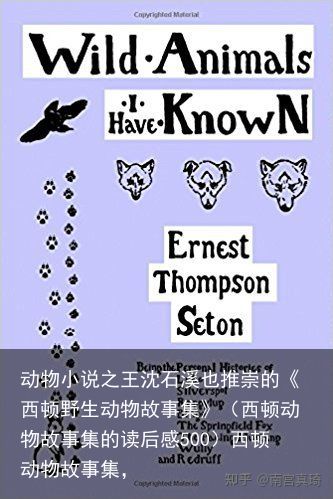长篇《凡人故事》:第〇七回 酒余饭饱员外献策 月明风清佳人重逢(故事会在线阅读2021年5月上)五五开讲故事第二集,
按:《中师生》公众号将从3月9日起连载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黄文斌的长篇小说《凡人故事》。这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共八十回,总43万字。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三个初出茅庐的中等师范生的工作爱情故事。
《凡人故事》
——爱情之花虽然珍稀,却总有人将她苦苦寻觅;只求有生幸得一遇,领略那千般袅娜、万般旖旎。
第〇七回 酒余饭饱员外献策 月明风清佳人重逢
且说玉磊正要回敬善俅荣的嘲讽,听得楼上一个声音在高喊:“乔老板,一包可以上菜了。”这声音猛听上去旁若无人,细细咀嚼却全是巴结献媚;好比纸糊罗汉,样子威猛,其实软包。玉磊抬眼望去,只见这人身着白衬衫、白西裤、白皮鞋;四肢肥硕粗短,肚皮圆滚凸起,脖子直接省略了,奶白脸庞上五官也接近退化,脑袋渐趋球体;五五开的分头,油光可鉴。杜玉磊厌恶之余又忍不住发笑,悄悄跟俅荣两个道:“看看这人,刷上一层绿,像不像《葫芦兄弟》中的蛤蟆精?”他俩也忍不住笑道:“真像。”
“我们也开饭吧。”蛤蟆精的话勾起了刘副主任的食欲。大家蜂拥进了包厢,刘副主任当仁不让坐了首席,其他人随意坐了。大家虽然是同届校友,以前在学校也只是面熟,现在突然“同是天涯沦落人”,距离仿佛下水的劳动布,瞬间小了号,几杯酒助兴后,越发亲近起来,话题也不限了。最令杜玉磊意外的是委培班的颜清也知道“杜冷丁”这个绰号。委培班和普师班的传统就是互相鄙视,常常三年不相往来。前者以后者是土不拉叽的农家子,后者以前者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弟。
谈兴正浓,玉磊忽然从半开的门缝中瞟见“蛤蟆精”挺胸腆肚从包间出来,用照例的腔调喊道:“清莲老板,上来敬一杯酒吧。今天的客人都是我最好的哥们,这个面子一定要给!清莲,清莲……”
一个看样子是服务员的女孩在楼下近前回道:“金站长,别喊了,说过一万遍,乔姐不吃酒的。”听语气这位服务员并没有给口中的“金站长”应有的尊敬。金站长笑道:“这我当然知道,不用喝酒,喝饮料。小梅,你再帮我叫一声嘛。”
小梅嘴里含混地说着什么大概是不满的话,野喊两声:“乔姐,乔姐。”未见应答,正待出去找,却见她就在门口傻站着,于是悄悄走到她身后“嘿”地一声:“想什么呢?”乔清莲吓了一跳,骂道,死丫头,魂都给你吓没了!“你什么时候变这样没胆了?”小梅道,“金站长又叫你去敬酒呢。”乔清莲说你回就是啊。“我回了,回不掉啊。”乔清莲见她板着一张脸,笑道:“有什么气可生的,他说让他说,我行还我素就是。”小梅道:“你当然不生气,你又没看见他那副死皮赖脸的样子。”“不好看谁叫你还看!”两人说笑着,厨房传出唐师傅的嚷声:“小梅,人呢,一包上菜了。”
客人见小梅一个人进来,小心地挤眉弄眼。金站长见大家这般表情,自己先笑道:“这没什么,金某的长处就是愈挫愈勇!”有客人道:“那倒是,大家还记得‘金龟子’怎么追咱们班的‘霍元甲’吧,那死缠硬磨的功夫可谓登峰造极。”“金龟子”是金站长高中同学给他取的外号,“霍元甲”是他们班一个女生的外号——当时热播电视剧《霍元甲》,这女生因死爱霍元甲而得了这个绰号。又一人道:“金龟子,我一直想问问你,霍元甲到底有没有被你泡掉?”大家起哄要他如实招来。金站长道:“那都是过去时了,提它干嘛;兄弟现在的目标是乔老板。按理我金龟子除了矬点,条件不差啊——怎么就这么难呢!不瞒你们说,我经常想,要是能搂着乔清莲睡一晚,第二天吃花生子也值。”“吃花生子”是垓地土话,意思是“挨枪子”。
一个诨名“冯员外”的今天喝得高兴,脑袋忽然机灵起来,献一计道:“看兄弟如此痴情,我给你出一个釜底抽薪之计。”金站长忙问什么釜底抽薪之计。冯员外看了一下门口。金站长会意,到门口瞧了瞧道,没人,快说。“别急呀,听我慢慢道来。”冯员外压低声道,“乔清莲没有正式工作,这是硬伤;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心气,不过依着酒家生意好,兜里有点钱;如果断了她的财源,我相信她立马要像霜洒的茄子——蔫了。”
金站长道:“主意是高。可人家味美价廉,做人又好,怎么才能断她的财源呢?”“味美价廉、人缘好开个胖嫂那样的小吃店是可以的;酒楼主要是做公家生意,做公家生意关系才是硬道理。如果另开一家有靠山的酒楼,这些就不顶屁用了。到时别人都不来,你却照旧在这里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何愁她不对你这个财神爷乖乖就范。”金站长大喜过望:“冯员外,你真是我的狗头军师。送佛送上西,救人救到彻,不如就你来开这个店。”冯员外道:“我没这个能量;但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人。”大家都问是谁啊。冯员外不说话,只拿眼睛看着桌上一人。“曹国舅!”大家异口同声道,“对对对,选他再不会错。”
曹国舅大名曹永隆,无业游民,仗着姐夫当乡长,天天在各站所里混吃混喝混拿。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其实鄙厌。曹国舅脑筋有点慢,还没大明白:“你们是在拿我开玩笑吧?”金站长道:“开你玩笑干嘛,这是你的财运来了,快好好敬冯员外几杯。”“好是好。”曹国舅见状也认真道,“只是这几年尽瞎折腾,败了不少钱,姐夫姐姐已经发誓不管我了——开店是要本钱的……”“本钱不是问题——这事我们以后再找时间商量。”金站长知道事情基本妥了,不想在酒桌上细谈,岔开话题,“今天本站长开心,大家喝起来!”大家都道喝起来喝起来。
按下金站长他们如何饮酒作乐不表。且说学区这边已经吃完,刘副主任带外地老师到乡招待所开房。本来可以两人一间,杜玉磊哥仨却自愿只住一间,刘副主任自然也不反对。没头没脑一天,大家感觉又累又乏,冲过澡好了些,玉磊说再下去走走。
和乐为笑道:“这才多会儿没见啊!”杜玉磊道:“爱去不去。”善俅荣道:“去,看美人又不是你的专利,为何不去?”玉磊道:“‘看’可以,不许动淫邪之念。”善俅荣道:“我们动就是‘淫邪’之念,你动就是‘纯真’之念,凭什么?”玉磊笑道:“公理——无须证明。”
三人又来到乔姐酒楼。小梅摇着一把折扇,坐在店门口歇凉,楼上传下闹酒的声音。杜玉磊叫道:“小梅。”小梅见杜玉磊长得帅气,又认得是刚才吃饭的客人,笑道:“你怎么知道我叫小梅?”
玉磊笑道:“因为小姑娘你长得‘美’啊,美——梅。”
“切!”小梅明知他是胡乱说的,就是挺开心,“你们坐吗?我去搬凳子。”
“谢谢,我们自己来吧,”三人各自搬把凳子坐了。玉磊道:“老板呢?”
“回家了。”
“哦,”玉磊失望地道,“楼上不是还有客人吗,老板怎么就回家了?”
“那帮人啊,一喝就到半夜,乔姐哪里会等他们。”
善俅荣道:“那帮人谁啊?看样子很咖。”
“林业站金站长的朋友。垓地最咖的就是金站长;人家名字也取得好——金鑫,都是金。”
垓地八山一水一分田,资源最多的就是木材、毛竹、笋干。木材、毛竹的砍伐证、出口证都是林业站审批,所以做木头毛竹生意的老板都得将金鑫菩萨一样供着。
“‘金鑫’?这名字不好。”杜玉磊笑道,“太多金,金是克木的——这个林业站站长迟早被他自己克掉。”
小梅笑道,你们老师还学过算命啊。
“学过一点。”玉磊开玩笑道,“你刚才为什么说老板不会等金站长?他可是你们的财神爷。”
小梅道:“财神爷不假,就是太死皮赖脸了。”
“死皮赖脸?”善俅荣不解道,“吃完不付账吗?”
小梅道:“那倒不会。我是说在追乔姐的男人里面,他最死皮赖脸。”
“哦,听你的意思,追你乔姐的男人很多了?”
“那是!”
…………
仿佛见到一幅名贵的画作被不懂行却要附庸风雅的人争相求购。杜玉磊忽然很不是滋味,招呼也懒待打,自个默默先离开了。
乔清莲这时并没有到家。她父亲在横街开了一个杂货店,每天晚上回家时乔清莲都要进去照个面。店里有一桌麻客,见乔清莲进来,都添加了精神,热烈地招呼。边上一个看客站起来让座:“清莲回来了,坐一下吧。”乔清莲忙示意她不要站起来:“谢谢香姨,我不坐了——小梅还要一会,有桌客人没吃完。”
香姨是小梅母亲,在杂货店边上开了一间豆腐作坊,得闲经常过来这边串门。香姨丈夫早年瘫痪在床,全靠她做豆腐营生。俗话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做豆腐。做豆腐苦就苦在每天得半夜起来磨豆浆,因此香姨大都在作坊里睡觉。阿莲父亲也经常在店里过夜,两人平时又会互相照看一下生意,人家明里暗里就开起了他俩玩笑。他们也不分辩,只当耳旁风;香姨每次看牌,还是亲热地坐在乔清莲父亲身旁。乔清莲和她母亲自然也听到些风言风语,但乔清莲母亲从未就这事质问过丈夫,做女儿的当然更不便追三问四。
“爸,今晚回家睡么?”阿莲问,“我好给你留门。”一个矮小身材,满头浓密黑发的中年人抬起眼皮道:“不回了,你把大门闩好。”这人就是乔清莲父亲,叫巫天禄。
一个麻客道:“明天是圩,你爸恐怕要和你香姨磨浆到天光呢。”说完三个麻客开怀大笑起来。
香姨立时涨红了脸;乔清莲爸却一副很受用的样子。
磨浆在垓地是男女之事的隐语。三个人之所以会为这句普通的双关语那样兴奋,多半是因为当着乔清莲这么美的女孩面——人的感受有时候真是非常微妙。
乔清莲知道最理智的应对就是不答腔。她告辞香姨出来,没走几步听到身后有人轻声唤道:“阿莲!”其时天色尚早,月光又亮,因此虽然声音不甚熟,阿莲并未受到惊吓,回头认得是杜玉磊,应道:“是杜老师!”
玉磊从酒家回来,正垂头丧气往招待所回,忽见乔清莲在前面,顿时心潮汹涌,想招呼担心太唐突,不招呼又不甘心,最终还是冲动战胜理性,鼓起勇气唤了一声。唤完这一声,他仿佛一个意识到亵渎了神灵的信徒,开始等待上帝的裁决。阿莲轻柔的一声“杜老师”,不啻上帝的无罪宣判。玉磊心内狂喜,不知所言,只应了个“欸!”
“怎么还在这?”虽然是夜色下,双方还是能感觉到气氛的窘迫。“房间热,下来走走。”杜玉磊极力想打破这种要凝固的空气,“垓地夜景还不错——凉风起来了。”话出口就后悔——太拙劣了。乔清莲暗自笑了笑:“嗯,明月清风,确实不错。景色是心情的折射——看来杜老师心情不错——你适才叫我‘阿莲’?”“是啊,”杜玉磊道,“前面听见有人这样喊你。”“那是我妈。阿莲是我的小名,除了妈妈和奶奶再没人这样叫的。”“哦,是这样。”杜玉磊又贸然道,“以后我也想这样叫你,可以么?”“以后?”仿佛这是个极神秘、神圣的问题,阿莲不敢轻易地回答。“是的,”玉磊急切地道,“以后!”阿莲的心弦被玉磊拨动了一下,妥协道:“嘴长在你身上,我也拦不住。”
“谢谢你,阿莲!”杜玉磊难以抑制地激动,“刚才在店里,冒犯了!”“没有呀,我倒觉得是自己冒失了呢——既然这样,算是扯平了。其实,杜老师过誉了,我只是姓乔,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好。”玉磊认真地道:“不是‘哪里有’,而是岂止有!”
“当老师的人总是喜欢浪漫的修辞——好让学生对你产生崇拜。”阿莲笑道,“对了,你分配在哪所学校?”
“坳村。”
“坳村?”阿莲心想还真巧——原来她也可以算是坳村人,因觉得有套近乎的嫌疑,没好意思说,只道,“坳村可是垓地最偏远的一个村。”
“最远能有多远?人类的足迹已经踏遍地球每个角落,甚至留在了月球;难道坳村还能比南极更荒凉,比月球更遥远?”说到这样的话题,杜玉磊总是那样豪气。“嗯嗯,杜老师的胸襟令人钦佩。我们的目光是不应该太短浅。”阿莲受到他的感染,“我到家了。杜老师,再见!”
可不,面前已经是刚才邂逅的那扇大门,月光中门楼更显庄严气派。杜玉磊不甘心就此别过,却找不到挽留的理由。闪念间,阿莲挺拔袅娜的身姿已经进了屋子,大门随即“吱呀”一声关上。
杜玉磊的魂魄似乎随着那声“吱呀”也被关到了门内,半天不能挪动一步。
作者:黄文斌,笔名:土村人。1988年毕业于福建南平中等师范学校。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图片来自网络)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