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故事集》节选:利玛窦之钟(青鸟pdf百度云)青鸟故事集,
时间是日光下移动的阴影,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是细沙长流。
后来人们才听到时间的声音。
阳光浩浩荡荡地泼洒在紫禁城金色的屋顶、血色的宫墙和空旷的广场,冬日的阳光坚脆,能听见阳光落下时发出瓷器开片般的细响。此外,再无别的声音。乾清宫外的廊檐下,宫女和太监们垂手侍立。他们的眼睛像绵羊,似乎在等待着那致命的一刀。“时辰快到了吧?”每个人都在心中自问,南天上,太阳似乎停止了移动,一棵枝丫清疏的老树把阴影投在窗上。等着,直到“当—”的一声从殿内传来,所有的人颤抖了一下,然后又是一声,一声接一声,清亮的铜音儿每一声都敲在心上。到底响了,人们似乎活转过来,靴声、衣带声、低语声,所有的声音嘈切如灰尘般浮动起来。每个人都惊喜地看了一眼太阳,此时,日正当午。
有些日子不为人知,但绝对重要。它们是小日子,人们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哪一年哪一天。那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的一刻,人们感受着莽荡的风,但谁知道这风最初的游丝般、鼻息般的律动起于何时?现在,我们知道一个日子:1601年 1月 25日,在这一天,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将两座自鸣钟呈献给万历皇帝。像一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皇上惊喜地听到其中一座钟准时发出鸣响,这其实也是现代计时器在中国大地上最初的、决定性的鸣响。它发自大地的中心、庄严的御座背后,声波一圈一圈无边无际地扩散出去,直到两三百年之后,钟表的滴滴答答声将响彻人们的生活。时间能够被听到,与此同时,时间也被看到。它不再是日晷的针影,不再是滴漏之水和沙漏之沙,影子仅仅是影子,水和沙仅仅是水和沙,它们不再表达和喻示时间的流动。时间就是纯粹的“时间”,是标记在表盘上的刻度,抽象而普遍,无论阴晴雨雪、无论昼短夜长,时间将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终于捕捉住了时间。
1601年是万历二十九年,距著名的“万历十五年”已有十四年。紫禁城正殿的御座依然空着,每逢庆典,朝臣们对着空空的御座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皇上了,有时某个朝臣会拼命地想:皇上长得什么样儿?但想不起来,皇上的相貌是记忆中一团模糊的影子。万历皇帝就这样以缺席统治着他的帝国,除了宫女太监,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在”。他行使着一种最终的权力:不行使权力的权力。后世的史家困惑地注视着这个怪物,他们眼看着大明王朝在他漫长、坚定的消极怠工中逐渐崩解。此人甚至算不上一个暴君,他的问题是他被“皇帝”这顶无比沉重的冠冕压垮了。如果这个名叫朱翊钧的人生在现在,他可以爱他的女人,他将把家业传给心爱的女人所生的儿子。但是不行,他是皇帝,于是大臣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来干涉他的家务事:那个女人是个妖精,太子应该由大儿子来当,小儿子不能当。—烦不烦呢?的确很烦。明朝是个奇怪的朝代,那时的人很奇怪。读书人读了一脑子圣贤书,然后就正气凛然,决心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为的大多是诸如此类的烂事儿:如果大儿子英明神武,争得也算值得,实际上那也是个糊涂虫,很可能还有点弱智。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位隐士隐于紫禁城。
那天,万历皇帝忽然问:“不是说有几个洋人要进贡什么自鸣钟吗?怎么还没有送来?”早在上年 7月间,皇上就接到了驻山东临清向来往大运河的商旅征税的太监马堂的奏报,说有几个洋人要晋京朝贡。10月,马堂遵旨呈上所贡物品的清单,计有: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自鸣报时钟二座、《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单子呈上来皇上却未作批答,既不说让他们来也没说不让来,一压就是两个月,似乎皇上把这件事给忘了。这很平常,万历皇帝处理国事的主要方法就是把它忘掉。所以皇上越来越胖了,据说他已经像一座移动的肉山,过多的脂肪淤积在声带上,使他的声音细若游丝,紫禁城里的当值太监们必定都长着兔子一般灵敏的耳朵。现在,他们听见了,皇上问起了自鸣钟!赶快让那几个洋人进京,把那自己会响的钟送来。
漫卷诗书喜欲狂,利玛窦后来肯定读过中国诗圣的诗,他将会想起 1601年1月那个寒冷的日子,在那天,终于接到了皇帝的诏旨,命令他们即刻启程赴京。他们已经在天津羁留五个多月了,漫长且似乎没有尽头的等待。有时利玛窦觉得也许会永远等待下去,他们将悬置在这里,被遗忘。实际上这不是不可能,利玛窦等人到京后见过一个突厥人,这个可怜的家伙从阿拉伯万里迢迢进贡一头狮子,然后他就开始等待朝廷批准他回去,他已经等了整整四十年,还得继续等下去。但就在绝望中,北京发出了召唤,“这完全出乎意料,仿佛是回答了很多人在各个地方请求上天保佑这次远征成功的祈祷。……他们相信是手里掌握着皇帝们的心灵的上帝以他自己的神秘的方式造成了这场突然的变化,以便拯救这些灵魂”皇上想的是自鸣钟,利玛窦却惦记着皇上的灵魂。这位传教士 1552年生于意大利小城玛切拉塔,早在青年时就发愿到“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撒下宗教的种子,以便来日大丰收”。正值西方的地理发现和殖民扩张,传教士们远渡重洋,踏上一片又一片陌生的土地。1582年,利玛窦抵达澳门,次年9月,他和一位同伴来到广东肇庆,开始了在中国毕其一生的传教事业。此时,北京高大的城墙已遥遥在望,利玛窦抑制住剧烈的心跳,他一步一步,走向他的梦想:中国的皇帝将皈依天主,然后……
1583年,也就是利玛窦来到肇庆的那年,在他的故国意大利,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注视着从教堂顶部悬吊下来的祭坛灯,那盏灯在摆动,摆过来摆过去,无论幅度大小,摆动的时间是一样的。手按着自己的脉搏,他感到那盏灯就在心脏中摆动。他叫伽利略,比萨大学的学生。当他在祈祷会上偶然看到教堂的灯时,自然的谜底、它的内在规律向着一个好奇多思的心灵敞开,那就是物理学中的“等时性”,使摆动时间发生变化的,不是摆幅的大小,而是摆动的物体的长度。于是,就有了钟摆。对机械计时器来说,这是决定性的进展,从此钟表的精确度就几乎是分秒必争—在此之前,一座钟一天慢上一小时也是寻常之事。仅仅十八年后,一座装置了伽利略式钟摆的大钟已经出现在紫禁城内,不过有个问题:钟不走了。
利玛窦带来了两座自鸣钟,一座大的,一座小的。小的高可盈掌,青铜镀金制成;大的镀金铁质,钟摆露在外面。1601年 1月 25日,发出鸣响的是那座小钟,大钟当然不会响,因为作为“当今世界最新科技成果”,它需要专业人员安装调试。
所以,传教士们可有的忙了,皇上迫不及待地希望听到那个巨大的怪物按着时辰发出响声,传召洋人火速进宫。利玛窦和一个同伴骑着马慌慌张张地赶到,只见那座金碧辉煌的钟正矗立在乾清门外的广场上。它太高了,一时无处安置。那一天是快乐的,沉闷单调的宫廷生活忽然波光荡漾,外庭的太监侍卫们奔走相告,去看那个自己会响的钟。不仅是钟,还有两个洋人,洋人的鼻子高,眼珠是蓝的或黄的,像波斯猫。大钟前黑压压挤了一地的人,最后不得不用大棒子把人群驱散。利玛窦也是快乐的,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帝国的中心,进入了这座传说中的神奇宫殿,他甚至来不及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他觉得在晕眩中穿过了巨大的梦境。他一直等待着这一刻,从澳门、肇庆、韶州,到南昌、南京,他一步一步艰难地向这里行进,整整走了十八年。利玛窦坚定地认为他将传播福音,但是现在,他得当一个钟表匠。此后直到清代,传教士的一门必修手艺就是修理钟表。
万历皇帝把小自鸣钟摆放在寝宫,精巧的小钟,利玛窦已经把钟面上罗马数字的时间标记改成了中文的时辰。皇上入迷地注视着指针的跳动,有时他就一直这么看着,直到小钟内部一阵躁动后发出“当—当—”的鸣响。皇上注视和谛听着时间,反正他有的是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很多年以后,另一位皇上—康熙皇帝写道: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此诗题为《戏题自鸣钟》,康熙另有一诗《咏自鸣钟》: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按指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显然,康熙的生活节奏是被钟表时间所支配的,“绛帻休催晓”,天已经亮了,但表上的时辰还没到呢,还可以再睡一会儿,但如果看表到点了,文件就必须准时送来。即使是现在,在中国的偏远农村,一个农民还是会依据日升日落、天黑天亮的自然节律安排他的生活,相比之下,二百多年前的皇上更像一个现代人,他摆脱了自然节律的羁绊,直接皈依于钟表所标示的物理时间。皇帝是天与人的中介,是天文、历法等事关天意的知识的垄断者,他本身就是时间的尺度,他的登基之年被称为元年,元而复始,直到下一个皇帝、下一个元年,时间完成了一次循环。所以,皇帝最先掌握了时间的秘密。本文节选自李敬泽作品《青鸟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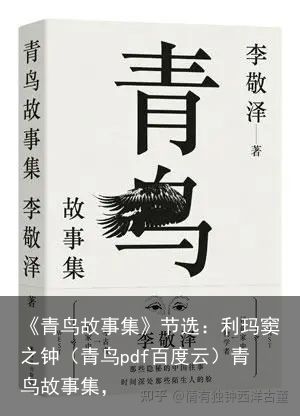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