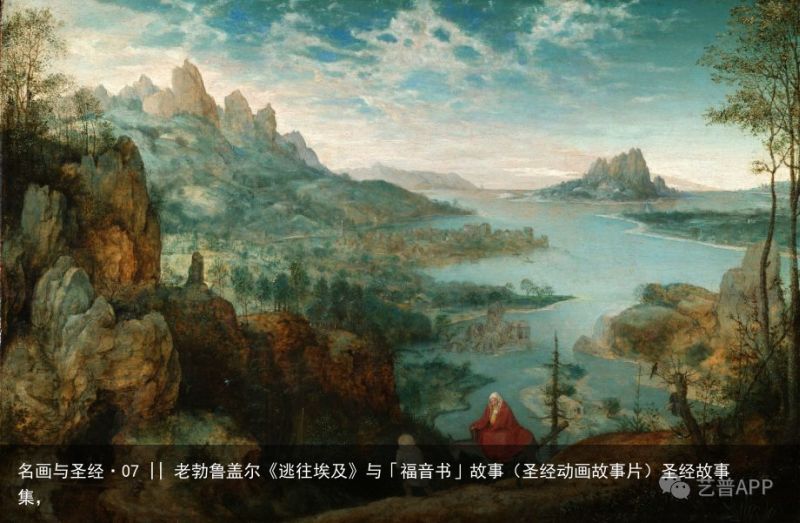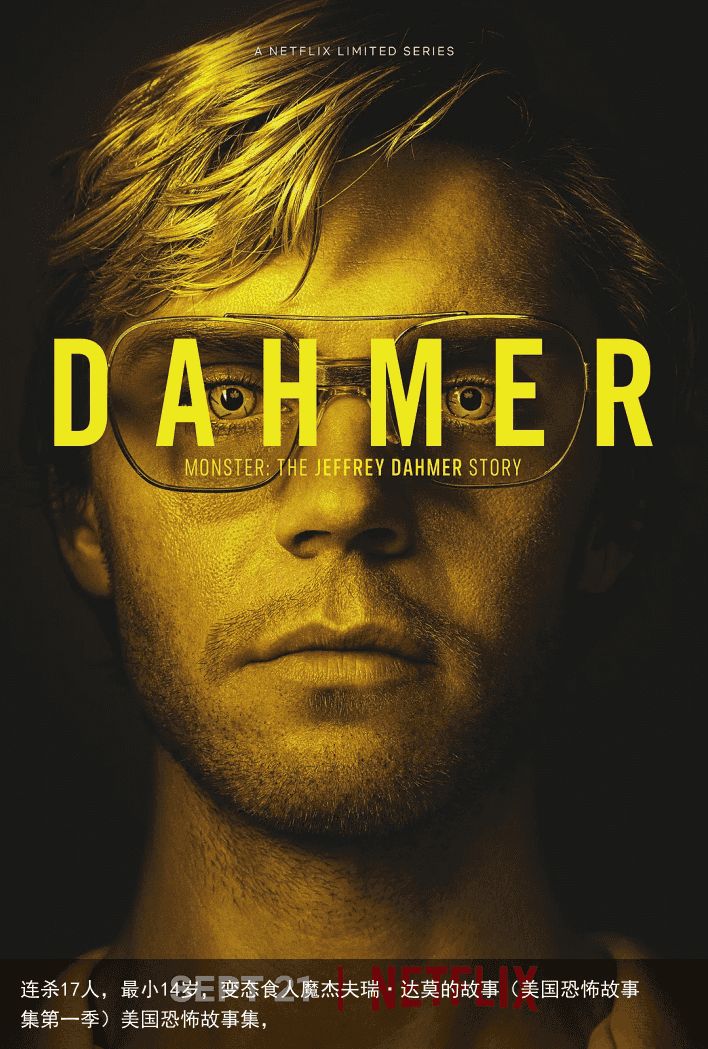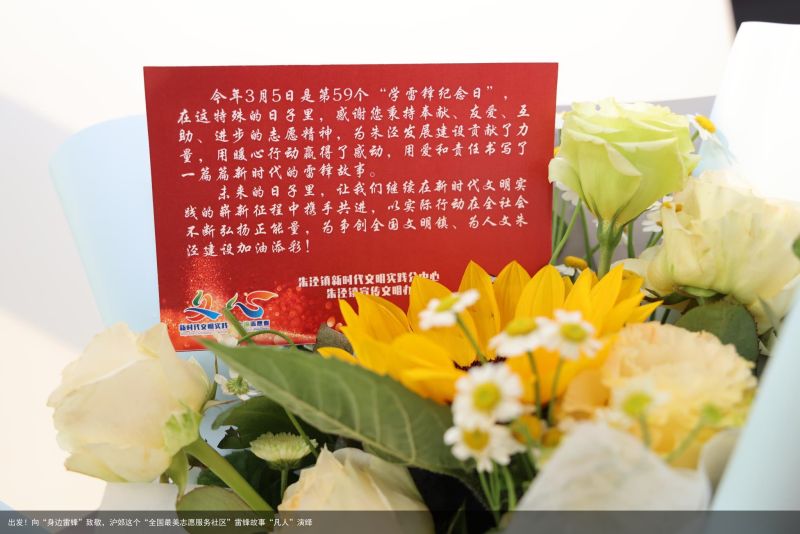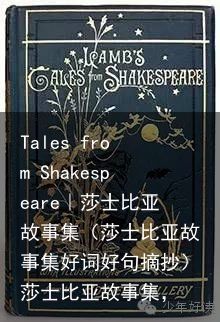她被迫离婚,被前夫称为土包子,却经营中国第一家时装公司(苏雅是谁)苏雅的故事第一集,
错误的开始
1915年,时年15岁的张幼仪正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三年前她在二哥张君劢(嘉森)和四哥张嘉璈的鼓励下进入这所新学堂读书。原本还有一年,她就可以顺利毕业。
而如今,正在课堂的上听课的她被匆匆接了回去。并没有和同学告别的机会。
刚到家,就听母亲喜上眉梢的跟她说,四哥给她找了个好郎君。
原来,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秘书的四哥张嘉璈,在一次学校巡视中,发现杭州一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这就是徐志摩。
四哥对徐志摩的才华很是赞赏。
而徐家又是江南远近闻名的富商。徐志摩生的斯文白净,又才华出众。
在四哥看来,如此门当户对,又才华出众的妹夫,实在是难得。
现在许多人认定张幼仪是高攀,其实不是。
张幼仪祖父是清朝掌管一方的知县,父亲是当地十分有名望的医生,她上面有八个各个和三个姐姐,对她疼爱有加。她的二哥张君劢是民社党的创立人,被后人称为民宪之父;而四个张嘉璈是中央银行的筹备着。张家在政界、金融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张幼仪二哥张君劢
而徐家能够和政治经济地位都不俗的张家联姻,对徐志摩的父亲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
两家人对这桩婚姻都非常满意。
对此,两个年轻人都一无所知。
从订婚到结婚,在同一年匆匆完成。
时年,张幼仪15岁,徐志摩18岁。
徐志摩
张家为次特地去欧洲置办嫁妆,新潮的沙发,玻璃橱柜,扶手椅,绣了花的棉麻衣服,各种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家具样式都有。嫁妆满满的装了一船。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婚前,母亲遵照旧礼,给女儿做婚前训诫:在夫家只能说是,而不能说不,一切要顺从。
她生在那个时代,母亲的话想来是对的。
而徐志摩就不同,他是真正的新学生。面对社会上的新思潮很是追捧,正是迫不及待想要抛旧迎新。
他刚刚从杭州府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正是意气风发憧憬北上求学,以至大展宏图之时,父亲突然硬塞给他一桩旧式婚姻。
徐志摩对这桩婚姻的评价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不从。
透着无奈及厌恶。
打心底已经认定这个硬塞给他的妻子,不过是封建社会的遗留。不值得他瞧上一瞧。
一无所知的张幼仪,带着她丰厚的嫁妆,怀着对陌生夫婿的甜蜜幻想,嫁进了徐家。
婚礼在徐志摩祖宅硖石商会举行。
当天高朋满座,宾客如云。因徐志摩要求要一个新式新娘,张家特别有心的让15岁的新娘张幼仪着粉红西式纱裙,戴中式凤冠。
一整天,不知磕了多少头,行了多少礼。
仪式终于结束。
被嫌弃的人生
新婚之夜,宾客散尽。面对这陌生的环境,满怀憧憬和激动的她并没有迎来温柔私语,而是独守洞房。
徐志摩连新房都没有进。而是躲到奶奶的房间睡了一夜。之后被长辈和佣人们簇拥着进了新房。也未对她说过一句话。
她默默忍受。
她侍候公婆,管理家务,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
然而这一切都温暖不了丈夫冷漠的心。
从看到她的照片第一天开始,徐志摩就不屑一顾的评价“土包子”。
他北上读书,接受更多新思潮,越发觉得自己的妻子土了。
可是,见过她照片的人知道,她不是倾国倾城的容貌,但是端庄雅致。
她也有一双好看的大眼。
张幼仪说,我也是被夸大的。
亲友对她的评价也是:其人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亲故多乐于亲近之。
连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也评价: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干练,给人极好印象。
是啊,她是家里的小妹,家境殷实,哥哥姐姐父母都十分疼爱她。
谁不是蜜罐里泡大的。
可是母亲说嫁夫从夫。
从新婚到徐志摩出国前的四年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至多4个月。都是在徐志摩的假期。
徐志摩在家时也不和她交流。
有一次,徐志摩坐在院子里读书,她坐在旁边做女红。徐志摩时不时的叫佣人为他做这做那。却不屑于和张幼仪说上一句话。
后来她在回忆录中说道:“徐志摩从来没正眼瞧过我 ,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基本是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徐志摩急切的想要出国。
在婚后第三年有了大儿子徐积锴,小名阿欢。
阿欢的出生并没有让徐志摩欣喜。这个儿子,不过是为了尽孝道而履行的婚姻职责罢了。
如今孝道已尽,孩子刚满4个月,他迫不及待的留洋去了。
全然不顾才生产的妻子,也没有过多眷恋新生的儿子。
在国外,那又是一片新天地。
在家苦守的张幼仪原本已经认命的准备独守一生。
没想到这时候,徐志摩给父亲徐申如来了书信。
“儿海外留学,只影孤单,儒慕之私,不佚罄述,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信写得情真意切,意为让父亲支助张幼仪去国外与他团聚。
张幼仪原本枯竭的心,又有了一丝希望。
她以为徐志摩回心转意。
家公对这个儿媳甚是满意,看到儿子盼着儿媳团聚,也非常开心。
父母终归是希望家庭和睦。催促儿媳张幼仪去往欧洲。
1920年冬,满怀欣喜的张幼仪安排好一家老小诸多事宜,便出发去往法国。
然而,她满心欢喜的盼望着,等来的却并不如意。
她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与丈夫徐志摩相见的场景:
“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的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色丝巾,虽然我重来没有看到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不想在那表情的人。后来张幼仪才知道,哪里有什么回心转意。
是二哥张君劢看到两人婚姻不幸福,现在又长期分离,恐怕对婚姻更加不利。何况妹妹也一直想要继续学业。才劝说徐申如放儿媳出国和徐志摩团聚。又一封封书信催促徐志摩接张幼仪到身边。
一切不过是情感和责任的加持,让徐志摩不情不愿所做的决定。
最要命的是,此时的徐志摩已经在几个月前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林徽因。
他正热烈追求林徽因。
张幼仪的到来倒是坏了他的好事一般。
让他如何耐烦。
虽然徐志摩不耐烦,嫌弃张幼仪读书不多,又沉默寡言,十分呆板无趣。但是既然来了,还是要带她见识见识。
他带张幼仪看过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等等,虽然张幼仪被他的冷漠态度伤害。可是能够见识到这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也让她有短暂的开心。
两人还拍了一张合照。这是两个人一生唯一的一次单独合影。
张幼仪随徐志摩几经辗转,暂居在索斯顿。在此处定居也不过是因为这里离剑桥比较近。
在这里,她彻底沦为佣人。
洗衣做饭,占据了她大部分时间。
她原本打算学习英文,可是教授英文的老师来了一次就因为太远,就再也没来。
一直以来,她以为徐志摩对她冷淡是因为在家有公婆,不好表现出亲热。
然而在索斯顿,徐志摩每天早早就出门去学校,黄昏才回来。
回到家,仍旧是沉默寡言,并没有想要和她沟通的意向。
这让张幼仪一度怀疑,徐志摩之所以每天归家吃饭不过是经济拮据所迫,又或者仅仅是因为自己做的饭菜还算和他的胃口。
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张幼仪虽沉默寡言,不抱怨,可是心里也是寂寞苦闷的。
偶尔想要和徐志摩说话,他就一副不屑的模样说,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仿佛和他说话都是不配的。
他从没想过,眼前这个做小服低的女人,也是进过新式学堂,也是有过天真烂漫的笑容,也是被人疼爱长大的。也是有血有肉的。
好在不久徐志摩带在此处留学的郭虞裳到家里居住。
张幼仪才偶尔有人同她说话、聊天。
坐火车还会因为肇事死掉,难道就不坐火车了么?
与对张幼仪冷漠无情相比,徐志摩对刚刚认识林徽因神魂颠倒。
在他心里美貌与气质并存,既懂中国传统文化又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林徽因才是女神。
当张幼仪每天困在家务俗事之时,他像所有出轨的丈夫一样,想出蹩脚的借口:去理发室理发。为的是去固定的地方收取来自女神的信件。
为了不让张幼仪发现,信件都用英文写成。
几个月后,张幼仪发觉自己怀孕了。
她想着有了孩子,是否能够让丈夫有所羁绊,对自己有所改观。
可是当张幼仪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志摩的时候,他一点欢喜也没有,只是不耐烦的跳起来说道:“打掉!打掉!”
张幼仪的心似掉入冰窟,可她仍旧忍着寒意小声说:“我害怕,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了。”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流产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通常还是一尸两命)。
而徐志摩说出的话让张幼仪一辈子也无法忘掉:“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而这番话竟然让张幼仪无从反驳。
在这不久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徐志摩在没有任何交代的情况下,独自往伦敦追逐自己的女神去了。
丢下举目无亲的张幼仪在索斯顿这栋乡下宅子里。
他没有想过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人生地不熟,还语言不通,怎么生活下来。
或许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女人的死活。
去往德国
走头无路的张幼仪无奈之下,给身在德国的二哥张君劢写信求助。
至此,张君劢才知道,自己一直费力撮合的婚姻成了这般样子。
可是作为徐志摩的脑残粉,他仍旧在信中说道:“张家失徐志摩之心,如丧考妣“,还是希望妹妹和徐志摩和好。并且承诺,让妹妹把孩子生下来,由他来抚养。
张幼仪握着这根救命稻草,独身去往哥哥给的德国的住处。
到达德国后,由于二哥没有照顾产妇的经验,就将张幼仪托付给了一对乡下夫妻照看。自己则时常抽空来看望妹妹,为她带来所需的营养品也陪她聊天、解闷。
这倒成了她在国外不可多得的一段平静温馨的日子。
至此,徐志摩既没有露面,连只言片语的信件也不成给她寄过。可见其自私寡情。
1922年,张幼仪在德国乡下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彼得。
小彼得
彼得出生没多久,消失许久的徐志摩就心急火燎的找上门。
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父爱心发作,要来看望自己的孩子。
这时,他好不容易得到女神林徽因的首肯,承诺与他交往,但前提是”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
他便得了圣旨般满怀喜悦的来逼迫刚刚生产完的张幼仪离婚。
此时的张幼仪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刚刚生产的劳累与痛苦还没散去。
没有迎来丈夫的嘘寒问暖。得到的是一纸离婚书。
她原本就是外秀内刚的性格,在徐家这些年越发的坚毅忍耐。见徐志摩如此绝情,她签下了离婚书。
从此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离婚案的女主角。
拿到签字的徐志摩心情大好,还跟随张幼仪去看望了小彼得。
张幼仪说:“他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得神魂颠倒”。
可是“他始终没问我要怎么养他,他要怎么活下去。”
这便是他作为父亲所做的最大的贡献了。
为了感谢张幼仪爽快的签字,他还特意写诗一首:《笑解烦恼结》,赠送给张幼仪。
(一)
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
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
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
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
四千年史骸不绝,
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
黄海不潮,昆仑叹息,
四万万生灵,心死神灭,中原鬼泣!
咳,忠孝节义!
(二)
东方晓,到底明复出,
如今这盘糊涂账,
如何清结?
(三)
莫焦急,万事在人为,只消耐心共解烦恼结。
虽严密,是结,总有丝缕可觅,
莫怨手指儿酸、眼珠儿倦,
可不是抬头已见,快努力!
(四)
如何!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
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
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
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
消除了烦恼!从此他彻底成了自由人,可以义无反顾的追寻自己的爱情了。
当徐志摩拿着这张小小的离婚书满怀喜悦与甜蜜赶回伦敦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女神已经跟随父亲回国,并很快就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结婚。
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此时,被动离婚的张幼仪还迷茫不已,望着嗷嗷待哺的幼儿以及决绝而去的男人,她陷入迷茫和恐惧。并不知道自己人生路该如何走下去。
痛失爱子
遍体鳞伤的张幼仪痛苦不已,她的世界坍塌了。虽然徐志摩来问她签字的时候,她大义凛然的签下了字。
可是,心里的恐惧不安无法用语言形容。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人登报离婚,她成了第一个。
她是一个如此传统而谨守本分的人,却做了一件“最时髦洋派”的事。
远在德国的她,不晓得那则不起眼的离婚声明,在国内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但是她晓得,这一次,自己彻底被抛弃了。
谁没有自尊心,谁的心不会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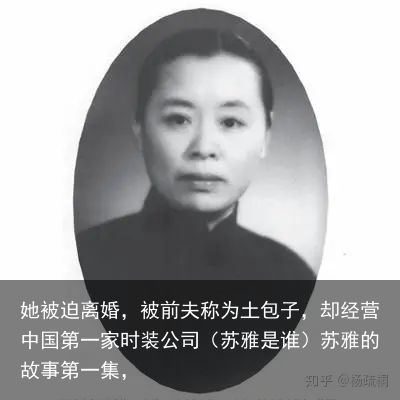
自此,她决定,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我要洗刷我的耻辱。
二哥对于两人的离婚,十分心痛。可是木已成舟,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此时正值德国马克贬值,早上还能买到毛皮大衣的钱,到了晚上,只能买条面包。
张幼仪把徐志摩父亲寄来的支票兑换成小额美元,她用这笔钱在柏林租了没有独立厨房、卫生间、客厅的小房间,并在二哥的物色下请了朋友朵拉来照顾儿子彼得。
三个人一起住在这小房间内。
她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规划。
一开始她先集中补习了几个月的德文课程。因为想儿子得到好的教育,她选择了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师课程。
在德国的这段时间,虽然非常的辛苦,但是少了徐志摩的横眉冷对,不用面对他的不屑与轻视,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看他脸色过日子,她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幸福。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场注定破碎的婚姻,现在看来,结束就结束。也没什么可怕的。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她自己又十分用功,在学业上进步也很快,而朵拉也成了她不可或缺的好朋友。
当她觉得自己的好日子就要到来的时候。
命运之神再一次击中了她。
1924年冬天,儿子彼得生了一场重病。原来因为从英国怀孕开始到生产后,她都没有得到好的照顾,彼得生下来后,就没有母乳喂养,一直是喝牛奶。
可能是买到了不新鲜的牛奶,让彼得感染了寄生虫。
当彼得突然大叫说肚子疼的时候,张幼仪和朵拉急匆匆将孩子送到医院。
可是经过多天的医治。小彼得在1925年还是离开了人世。此时他才刚满三岁。
彼得对于张幼仪的重要性来说,不仅仅是母子。
从英国到法国,从离婚到振作起来,彼得是独在异乡的张幼仪唯一的精神支柱。
无论多困难,她一想到还有孩子需要依靠她,便振奋起来。
失去幼子之痛,痛彻心扉。她失眠痛苦到无法进食。
然而在彼得离世一周后,徐志摩来到张幼仪的住所。
除了来要离婚书的时候匆匆在医院见过孩子一面之后,这三年他无只言片语。如今孩子死了,他倒是来了。
只是此时的张幼仪心灰意冷,已经不想和他争辩。
她忍者痛苦,带着徐志摩去殡仪馆见儿子最后一面。
见过儿子的徐志摩又做了一篇文章《我的彼得》,以此来怀念这个“儿子”。
写得情深意切,一副痛失爱子的姿态。
算是对这个从出生到离世都不成得到父爱的孩子的一点慰藉。
在看过儿子之后,他就提出要带张幼仪去意大利散心。
此时的张幼仪在经历丧子之痛后,正茫然不知去往何处。便答应同他前往。
可是徐志摩的邀请也让她不解,在离婚前徐志摩对她从来没有这么热心过。
不过很快,她就知道了答案。
原来徐志摩并不是见她痛苦要陪她散心。而是为了出来躲避风头。原来与张幼仪离婚后的徐志摩心急火燎的回到国内追求林徽因。
可是在徐志摩疯狂追求下,林徽因仍旧理智的决定跟梁思成结婚。因为在她看来,徐志摩是一个很好的恋人,但是这种恋爱的狂热来的快,去的也快,不适合做丈夫。
失恋不久的徐志摩在1923年又陷入了与陆小曼的热恋之中。
然而陆小曼不同其他人,她是有名的交际花,最重要的是,她是有夫之妇。
她的丈夫王赓也是梁启超的学生。算是徐志摩的同学。
一个离婚的男人和一个是家有丈夫的女人,都是社会名流,一时在北京的名流圈传得沸沸扬扬。
很快,徐志摩在北京就待不下去了。
他想到国外避避风头。如此才找到了张幼仪。
这让张幼仪更加清楚了这个男人的秉性。
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他想到的永远都是自己。
出彩的人生
1926年,张幼仪与八弟张禹九一起回到上海。
当她从轮船上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往事如烟。她仍旧记得6年前,她怀揣对丈夫的希望去往陌生国度的心情。
不过6年,丈夫没了,儿子没了。
她伸出自己的双手,默默对自己说,一切都只能靠这一双手。
回国不久,她就去徐家将长子阿欢接出来,带着孩子去往北京读书。
对于小彼得的离世她一直心怀愧疚,对于长子,她更加珍惜,想一直守在儿子身边,让他接受好的教育。直到张母去世,她才携子回沪。
徐家长辈对这个知书达理又恭顺贤良儿媳一直充满感情。徐父徐母在她离婚之后将她认做义女。此后徐申如几乎将徐家所有产业交由张幼仪打理。可见对她的信赖与倚重。
此时,四哥张嘉璈已经是中国银行副总裁,主持上海各国银行事务。
而徐申如也把海格路125号(华山路范园)送给张幼仪,使她和阿欢能够在上海衣食无忧。
张幼仪先是在东吴大学教授德语。
后来在四哥张嘉璈的支持下出任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
与此同时,八弟张禹九与徐志摩等四人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又聘请张幼仪出任该公司总经理。
云裳服装公司为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张幼仪把欧美的新式样引入‘云裳’,因为裁剪缝制考究,成为一流时装店。
顾客多为大家闺秀、海上名媛,在社交场中,都以穿着‘云裳’所制服装为荣,因而生意兴隆。
1934年,二哥张君劢主持成立了国家社会党,她又应邀管理该党财务。
她为人严谨,做诸多事物都一丝不苟,在国外的经历见识又让她敢于创新。她做银行副总裁之时,银行已经呈亏损,她上任不到一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做服装公司总经理,也将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成为上海名媛争相穿着的名牌。
她事事尽力,事事做好。也是要争一口气的。
此时,她与徐志摩反倒关系变得亲近起来。
而徐志摩与陆小曼在一起之后,因陆小曼的名媛作风,两个人都花费无度,经济上一直紧张,张幼仪不计前嫌,反而时时接济。
在徐志摩飞机失事之后,后事也是由她负责处理。其后,陆小曼在生活上也多受她的恩惠照顾。
徐志摩多次在与友人通信中说过,她(张幼仪)如今是个顶了不起的人了。
他没有看见是经过了如何的蜕变才有了今天的张幼仪。
此时的张幼仪已经无需他人评说。她已经成了自己的主宰。
解放前夕,张幼仪赴香港定居。
1953年,张幼仪在香港与邻居中医苏纪之结婚。
这位苏医生,也是离异,有子女。
在婚前,她写信到美国征求儿子阿欢的意见
理由是“因为我是个寡妇,理应听我儿子的话。”
儿子的回信:“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此时阿欢已经在美国做土木工程师。
这封信读来情真意切,字字深情,让人泪目。短短数十字,包含了张幼仪这艰难的一生如何度过。
此后张幼仪一直随苏医生生活。
1972年,苏医生病逝,她去往美国。1988年,于纽约去世。
后来有人问她爱不爱徐志摩,她答道:“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往事如烟,在耄耋之年再回想起来,这一切也不过如此。爱与痛都不再重要。那口争来的气,成了她漫长人生的精神指引。
此生再不相见,来世也不想再见。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