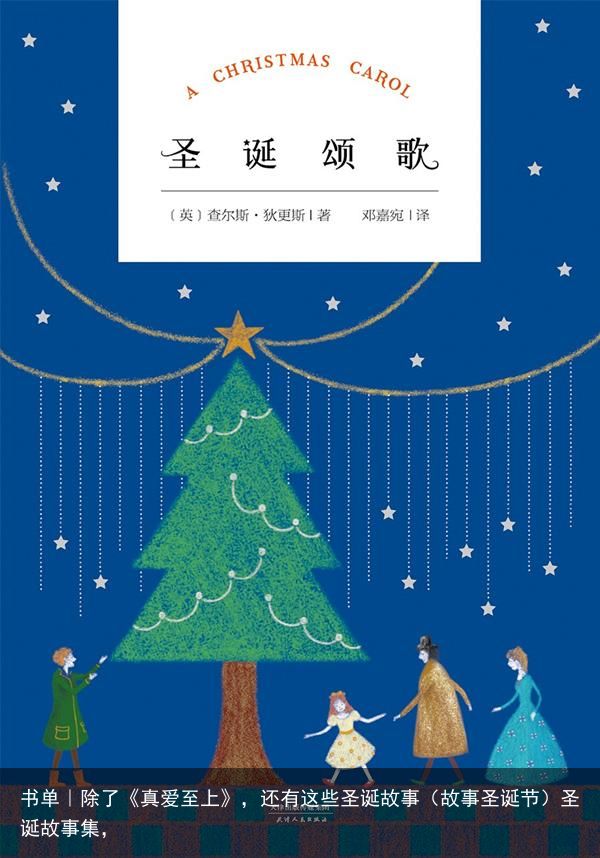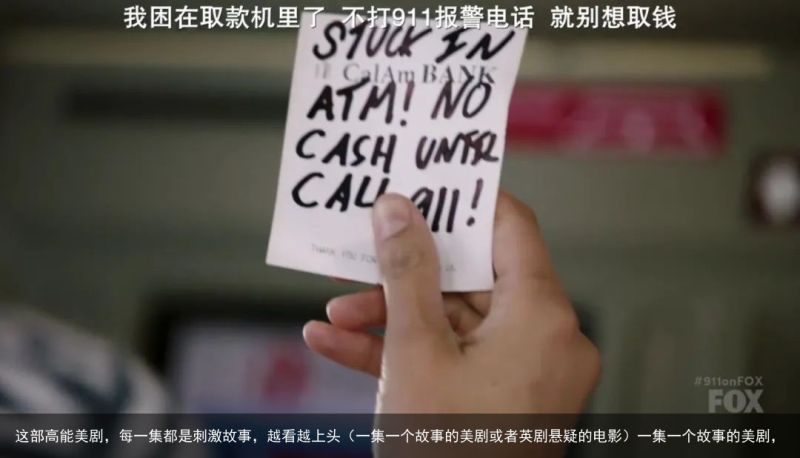故乡大地上的动物们(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阅读导引单答案)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
近日读加拿大作家西顿所著《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被书中记录的动物的真实故事所感动。我非动物学家,也非要深入研究动物,只是这本书让我想起六七十年代,在故乡大地上生活的那些或飞翔或奔跑或爬行的动物们。
一
记忆中,六七十年代故乡所在的渭北旱塬,生态相对原始而多样,野草杂树丛生的沟壑梁茆,四季变幻色彩的田间地头,炊烟袅袅的村舍庄院,是许多野生动物休憩繁衍的家园。儿时贪玩又好奇的天性,让我和小伙伴们疯跑于村里村外、田野沟坎,没有什么环保意识和动物知识的我们,掏鸟窝、撵野兔、捉虫子、套野鸽,一年四季乐此不疲。
如同故乡沟壑纵横、干旱贫瘠的大地,生息于此的动物都普普通通,绝不会有像大熊猫、朱鹮、老虎这样的珍鸟异兽,连上得了动物保护名录的都寥寥无几。从大人们口中知道的,当时似乎还尚存的金钱豹、狼、狐狸、獾等野兽,我只见过狼和狐狸。至于金钱豹和獾,不知是活动隐秘而难以见其真容,还是已经从故乡大地上绝迹,不得而知。而我和狼的三次相遇,因其有些戏剧色彩而至今难忘。
那年我不到五岁,刚过完春节,记不清是大年初几,母亲带着我回外婆家。从我家到外婆家有近20里崎岖不平的山路,且天还下着雪,到处冰天雪地。母亲背着我走到一处陡而险的山路前,实在是背不动我了,就把我放在了坡下住着的一户人家,然后她回去让我舅舅来接我。
舅舅来后谢过那家人,冒着风雪,背着我爬过那面陡坡,在白茫茫的荒野上坎坷前行。走到一处四野开阔、两边是高低不平的庄稼地时,三舅突然停了下来,并说了一声“狼!”。顺着三舅望的方向,我看到四个狗一样的动物从不远处的田埂下尾随而行,只不过它们的尾巴长而粗,也不像狗的尾巴那样卷曲着。舅舅背着我僵站在路上,一声不吭。好在那四只狼在经过我们面前时,只是犹豫了一下,并没有停留,也没有想伤害我们的意思。最后,随着头狼步伐的加快,它们排成一溜相互跟随着走向远方。
我与狼的第二次相遇,已经是七八年之后的事了。那时每到假期,我年幼干不了地里的农活,就与本家的一个大哥一起给生产队放羊。那天临近中午时,正坐在草地上昏昏欲睡之际,从沟里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声“狼吃羊了!”的喊声,一下子惊跑了我的困意。看清在沟的对面,两只狼正在撕咬着一只绵羊。此时,在沟边及沟里干农活、砍柴的人纷纷闻声而来,众人赶狼的吆喝声在沟壑两岸此起彼伏。
人们的喊声不仅延缓了狼撕咬羊的节奏,也逐渐瓦解了它们的斗志。那两只狼面对已经快到口的食物,不想轻易就此认输,又惧怕着人们的呐喊与驱赶。我看到它们一会儿咬住还在不停挣扎反抗的羊,一会儿又放弃,这样来来回回两三次。最后,随着沟上沟下人们喊声的不断逼近,狼最后还是极不情愿的丢下羊,消失在了沟壑深处。
通过这两次与狼相遇的经历,使我对从大人们口中听到有关狼的可怕、凶残、狡猾,甚至一些离奇恐怖的故事,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我最后一次在视野之内看见野狼,已经是七十年代后期。地点是老家后沟,时间大概是深秋,天蓝气清,望眼沟里沟外,一切尽收眼底。已经没有多少绿意的杂树草丛中,时不时地传来几声野鸡的鸣叫和翅膀的扑楞声。当太阳西斜之际,我坐在已经捆好的柴垛上等待着其他伙伴。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了狼,是一对。在夕阳的余晖中,它们一前一后,沿着曲曲弯弯的沟底向着下游跑去。我静静地看着它们仓促而苍凉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沟壑深处。
这事我没有告诉同行的伙伴,就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很少对人提起。这次相遇,可能成为我今生在野生环境下对狼的最后一瞥。
二
而我看见狐狸的过程,却是人与动物之间激烈的冲突,充满了血腥。
故事发生在我外婆家,那时我五六岁。我舅家村子的几十户人家,背靠着一条土崖挖窑筑院而居,村子前面是一片荒原,再远处就是沟壑,那里常常有狼、狐狸、老鹰等野兽猛禽出没。为了防止野兽侵害家畜家禽,几乎家家都养着狗。每到夜里,村子里狗此起彼伏的叫声不绝于耳,让漆黑而神秘的村野显得更加苍凉。
在村子前面的荒草地里,有一孔被废弃多年的水窖,边上不仅长满了蒿草,还有各种荆棘杂树,经常有小动物甚至家畜不注意就掉入其中。有一天,一只偷吃家鸡的狐狸,被撵得慌不择路,一下子掉进了水窖里。
在故乡人的心里,狐狸不仅邪恶,而且狡猾,是必须除之而后快的敌人。人们吆喝着,用砖头瓦块砸着在窖底上蹿下跳的狐狸,想将其置于死地。水窖底大口小的形状,使得狐狸无处挖抓,不仅上不来,还挨了几砖。后来,狐狸干脆钻到窖底的凹处,不再扑腾挣扎。看着这种情形,有人拿来绳索,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下到窖底,将龇牙咧嘴不断发凶的狐狸捆绑并吊上了水窖。
在众人的吆喝声、狗的狂吠声中,瑟瑟发抖的狐狸被弄到了附近的碾麦场。被绳索捆绑着难以脱身的狐狸,尽管拼命地挣扎,并发出阵阵凄厉的叫声,但最后还是被人们用撅头、锄头等农具杀死了。
至今想起狐狸血染碾麦场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在我儿时的经历中,故乡人对待动物并非都这样残忍,对于那些无害甚至危害不大的动物,能忍则忍,绝不赶尽杀绝。
比如对待蛇。故乡人认为蛇是有灵性且会记仇的,伤害一个会招来更多。所以尽管蛇是人们最惧怕的动物,但轻易是不会招惹的。据说有一个城里来的小伙子,把一个蛇开膛破肚,取出蛇胆泡酒喝,结果去村子一处水窖担水时,碰到一条更大的蛇挡在路上,吓的魂飞魄散。幸亏附近的人们听到他的呼喊,赶来把蛇赶走,他才得以脱险。
有一户人家家里钻进一条蛇,这家主人半夜起来上厕所,黑咕隆咚一脚踩在了出来觅食的蛇身上,人和蛇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相遇所惊吓。那家主人在慌乱中惊叫连连,随之匆匆逃进了屋子。
第二天,这家人叫来了一些抓蛇有经验的人,想把那条蛇弄出自家庄院。我们一帮小孩就跟着大人们去看热闹。只见人们东找西找,最后在一堵土墙的缝隙里发现了蛇的踪影。可蛇不可能自投罗网,钻在墙缝里就是不出来。最后只得把墙挖倒,蛇才露出了真面目,那是一条两米多长的菜花蛇,也是故乡常见的蛇类,是没有毒的。但人对蛇生来似乎就有一种恐惧,尽管没毒却没人敢上前动它。有人拿来了扫帚,想让蛇爬到扫帚里,然后再弄出去,这是故乡人对付蛇最普遍的方法。
这时,我看到有个人一把提起蛇的尾巴,一边抖索着一边朝外走,引来围观的人们一阵阵惊呼。那人将蛇提出院子,放生到一处废弃的水窖里,想着这下就不会惊扰到人了。谁知没过多长时间,在那户人家的院子里,又发现了蛇的踪影,至于是不是那条被请出去的蛇不得而知。
这户人家再也没有要把蛇弄出家园的举动,它们想着弄出去它可能又会回来。无可奈何之下,干脆就由它去了。
三
每到春夏之际,各种小动物们就吸引了我的目光。在庄院的墙缝中、未住人的窑洞里、村前村后的树丛上,以及山梁沟峁间,居住着燕子、戴胜、鹞子、喜鹊、野鸽、乌鸦、野鸡等飞禽,在田野的庄稼地里,有野兔、黄鼠狼等动物出没。
有一年一对戴胜(故乡人叫它“臭姑姑”),在我们家庄子土坯墙缝里筑巢安家,看着它们忙忙碌碌、飞出飞进的身影,听着他们粗壮而低沉的“扑扑扑”的鸣叫,我常常抑制不住想爬上它们的巢里,去窥探究竟,但直到戴胜的幼鸟一一飞出巢穴,也没有把这种冲动付诸实施。我曾近距离看到这种头上顶着扇形羽冠、穿着花格裙子、嘴又细又长的鸟儿,在沙土里翻滚抖动,如牲口在土里打滚一样。它们可能也是为了让身体更舒服一些吧。
还有一种故乡人叫作“火燕斑”的鸟儿(学名叫作北红尾鸲),大小如麻雀,雄鸟与雌鸟形象各异,但都很漂亮,叫声婉转动听。它们和麻雀一样,喜欢把巢筑在无人居住的窑洞的墙缝里。它们几乎年年都来,而且是踏着春天的脚步,用歌声早早地向人们报告春的信息。一个春天,在家里庭院的树丛中,都能看到它们蹦蹦跳跳的身影,听到它们动听的歌声。
小时贪玩的我,对于生活在庄院以及田野里的任何小动物,都有着想亲近甚至喂养的渴望,虽没有伤害它们的故意,却往往事与愿违。
那时每到夏天,我们最爱干的事儿就是掏鸟窝。当然,喜欢把巢筑在高树高崖之上的喜鹊、鹞子、乌鸦、野鸽等鸟儿的窝,没有大人帮助,我们只能远观。还有一些远离村庄、行动诡秘的鸟儿,连见到其窝都难。所以,常掏的只有麻雀的窝。因为麻雀不仅多,而且多以人类居住地周边为其巢穴。
我最爱掏的是幼鸟即将离巢的麻雀窝,因为那些幼鸟可以养起来,用长长的线绳绑在腿上,时不时地放开,看着它们飞而又飞不远。曾经一次捉过五六只麻雀幼鸟,可怜那些麻雀的父母,围着雏鸟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现在想来,那些麻雀父母是在撕心裂肺的呼唤着儿女,抗议着我们对其的侵害。
那些从巢穴捉来的小麻雀,最后都以进了猫腹的悲剧而结束。有时我会为此而伤心,熟不知麻雀性硬,是很难当做宠物鸟养的。但那时,我怎么知道这些呢。
我还养过一只受伤的野鸽子。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冬日,我舅舅路过村上一处碾麦场时,惊扰了一群正在麦草垛里觅食的野鸽子,呼啦啦飞起一大片,有一只鸽子不知怎么就飞不起来,舅舅走进一看那只鸽子翅膀受伤了,就把它带了回来。
在我的央求下,母亲同意我把它带回家养起来。对养鸽子一无所知的我,在屋外用砖头搭建了一个临时的鸽子窝,到了夜晚怕野猫或黄鼠狼侵害,将其放入土炕底下放柴草的仓室。每天我都想法给鸽子喂一些小米、玉米、高粱之类。偶尔会把它带到野外,让它在地上走动,有时看见成群飞过的鸽子,它会望向天空,并扇动翅膀企图跟上鸽子的队伍,但每次都飞不了多远就落了下来。我是盼望着它的伤早点好起来,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去为它疗伤。
有一天,它突然死了。为此,我还伤心了很长时间。
当然,我还养过其它小动物,比如野兔、松鼠等,但都以不得善终而结束。这样的经历,使我对故乡大地上的动物们产生了几分敬畏。它们一旦失去自由,大都会抑郁而死。
故乡大地上伴随我童年时代的动物们,有些已经在岁月中消失了踪迹。它们曾经给予我惊奇和快乐,赋予我初识生命的多种体验,也让我更加珍惜一切生命。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