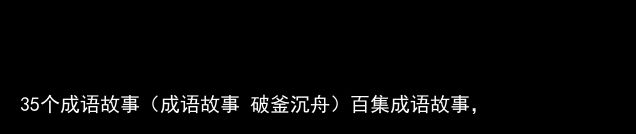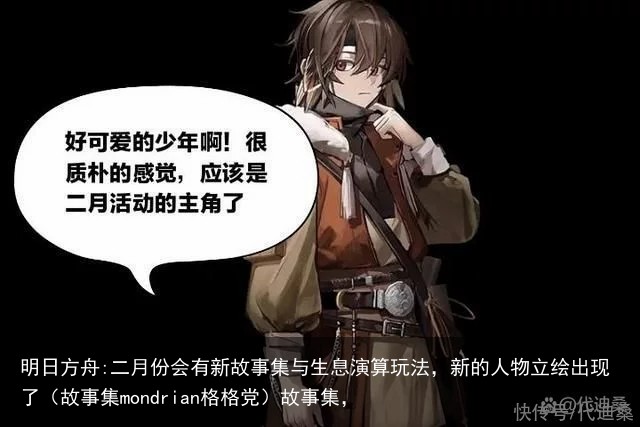作为细节、想象和误解的历史——《青鸟故事集》跋 文/李敬泽(青鸟故事集下载)青鸟故事集,
感谢布罗代尔。在他的书之后,我写了这本书。
1994年夏天,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我第一次读布罗代尔,读他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夜幕降临,江水浩荡,汽笛长声短声,平生远意。在那时,布罗代尔把我带向15世纪——“现代”的源头,那里有欧洲的城堡和草场、大明王朝的市廛和农田。我们走进住宅,呼吸着15世纪的气味,察看餐桌上的面包、米饭,有没有肉?有什么菜?走向森林、原野和海洋,我们看到五百年前的人们在艰难行进,我们注视着每一个细节:他们身上衣裳的质地,他们的车轮和船桨,他们行囊中银币的重量,他们签下契约时所用的纸笔……
布罗代尔说,这就是“历史”,历史就在这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
这不仅是历史,也是生活。在时间的上游,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但对我来说,它们仍在,它们暗自构成了现在,它们是一缕微笑,一杯酒,是青草在深夜的气味,是玻璃窗上的雨痕,是一处细长的伤疤,是一段旋律,以及音响上闪烁的指示灯在黑暗中如两只眼睛……这一切依然饱满,它们使生活变得真实,使生活获得意义。
“历史”同样如此。布罗代尔使我确信,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他们的贪婪和愚蠢。历史的面貌、历史的秘密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定,一切都由此形成,引人注目的人与事不过是水上浮沫。
所以我寻找他们,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里的人,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的踪迹,倾听他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声音……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撰写这样一本书是一种冒险:穿行于博杂的文本,收集起蛛丝马迹、断简残章,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与遗忘的荒漠,沉入昔日的生活、梦想和幻觉。
这肯定不是学术作品,我从未想过遵守任何学术规范。恰恰相反,它最终是一部幻想性作品。在幻想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动展现,就像两千年前干涸的一颗荷花种子在此时抽芽、生长。
这本书在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之间展开,这首先是因为那些人和事真的非常有趣;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个所谓“全球化”时代,我强烈地感到,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缭绕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乐观主义往往是由于健忘,就像一个人只记住了他的履历表,履历表记录了他的成长,但是追忆旧日时光会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没有离去,一切都不会消失。
这本书于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题为《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一本小书而已,十六年来从未再版,其中的作品也从未收入其他文集。我一直觉得,这是没有写完的书,我一直想象和规划着一本更大的书。
然后,就是这本《青鸟故事集》。它并不符合我的期待,更大的书至今没有写出。这本书对《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做了修订,增补了《抹香》《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巨大的鸟和鱼》三篇,其中的《抹香》写于2016年4月。
书名中的“青鸟”参见书中《飞鸟的谱系》。汉语中,翻译之“译”字源出于鸟。此义不仅汉语如此,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讲述畏吾儿(维吾尔)人的起源:畏吾儿各族推举不可的斤为汗,“他们汇集在一起,举行盛会,把他推上汗位。全能真主赐给他三只尽知各国语言的乌鸦(Zāgh),他在哪儿有事要办,乌鸦就飞到那儿去侦察,把消息带回”。
Zāgh原是古波斯词乌鸦,何高济译本译为乌鸦,但也可能是喜鹊。前者是鸟纲鸦科鸦属,后者是鸟纲鸦科鹊属,本来同属一科。无论是鸦是鹊,报喜或报忧,总之此鸟精通外语,职司侦伺。
由此想到《山海经》中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后来,这三只鸟飞进太阳黑子,成了乌鸦。天有一日,乌鸦也只有一只,但“三青鸟”的“三”却如孙猴子的尾巴,粗枝大叶地留着,变成乌之三足。
三只青鸟幻化为三足乌,但青鸟并未在天空消失,它们继续飞翔,到唐代,其职责已经由取食变成了传信:“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此时,它们和西王母没什么关系了,主要和“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有关,跨越蓬山之远、云外之遥,传递人类的心意和情感。
西王母所居正在如今的新疆。当日她接待周穆王,大摆筵席,宾主间想必需要翻译。所以,事情也许是这样的:酒席上西王母身边那三只巧舌的鸟儿向东飞去,变成青鸟、三足乌,但同时,那鸟也留在西域诸民族之间,后来成为不可的斤汗的乌鸦,不是一两只,不是四五只,恰好也是三只。
这本书写的皆是此地与云外异域之间的故事,书里的人原也是西王母座前之鸟,所以,名为《青鸟故事集》。
另有一件事差堪自喜。十六年后,重读当日写下的那些故事,觉得这仍是我现在想写的,也是现在仍写得出的。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